|
|
|
|
|
eLight诺奖对话专栏 | J. Michael Kosterlitz |
|
|
导读
以史为鉴,方可行远。回望科学史上振奋人心的发现瞬间,eLight特设“诺奖对话”专栏,让活着的传奇,带我们徜徉科学的高光时刻。专栏开设后,迅速得到了2016年、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J. Michael Kosterlitz 与Pierre Agostini 的鼎力支持。
本期对话聚焦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J. Michael Kosterlitz。出生于科学世家,其父亲Hans Walter Kosterlitz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快乐源泉”内啡肽的发现者之一。父亲的才华、意志力以及挑战传统的勇气塑造了J. Michael Kosterlitz 的价值观。因此,自科研生涯伊始,J. Michael Kosterlitz始终致力于探索事物的本质,享受科研的乐趣,而非逐鹿功名。在采访中,他数次提到“Scientists are paid to have fun”,感叹自己何其有幸,能够获得报酬和资助,去探索科研,从而追寻快乐。热爱是成功的基石,在其学术生涯中,J. Michael Kosterlitz与David Thouless 合作,颠覆了传统认知——即二维系统因热涨落而无法发生相变。 他们揭示了涡旋-反涡旋对在相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拓扑相变,即如今闻名于世的科斯特利茨-索利斯相变(Kosterlitz-Thouless相变,简称KT相变)。而其将数学分支拓扑学引入物理研究的革命性想法,开辟了拓扑学+物理学的交叉研究,也与eLight拓展光学边界、探索跨学科研究的宗旨高度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J. Michael Kosterlitz在其公开讲座中,推荐读者通过阅读这篇eLight对话来了解他——这无疑是对eLight及本次对话的最高嘉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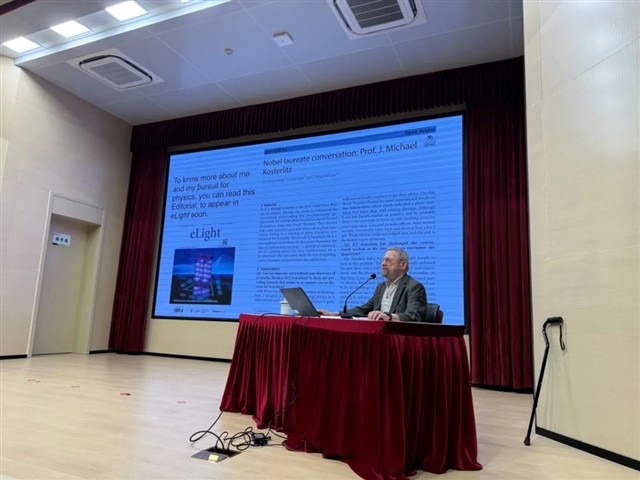
受访者:J. Michael Kosterlitz
采访者&翻译:杭志宏、郭宸孜、仇成伟
原文信息:Hang, Z.H., Guo, C. & Qiu, CW. Nobel laureate conversation: Prof. J. Michael Kosterlitz. eLight 5, 11 (2025).
https://doi.org/10.1186/s43593-025-00090-0
Q1:您能分享发现KT相变背后的故事吗?在您发现KT相变之前,是否有任何相关或启发您的研究?
A1:当我到伯明翰大学做博士后时,我正计划从高能物理领域转向其他方向,也考虑过转向凝聚态物理。那段时间,我与几位教授进行了交流,以征求他们的建议。有一天,戴维·索利斯(David Thouless)向我展示了一些关于氦薄膜的实验结果。这些结果清晰地表明存在一种相变,但与当时的理论相违背。虽然我并非索利斯的学生或博士后,而且他当时的想法比较模糊,可能也没指望我能搞出什么名堂,但我还是决定努力试试。几个月后,我带着研究结果再次找到他,我们决定共同撰写论文并发表,后续的发展便成为众所周知的科学史了。
Q2:KT相变挑战了当时的传统认知,您遇到过质疑吗?
A2:当时的情况非常尴尬,理论和实验存在冲突,而理论看起来又极其合理。David Thouless和我恰恰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因为那时我对凝聚态物理完全不懂。但幸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无知”反而成了优势——它让我得以摆脱传统框架的束缚,自由地探索新想法,不受任何预设观念的干扰。我们之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传统理论仅考虑了低能级的激发,但事实上是高能级的涡旋激发才是破坏超流的根本原因。
Q3:是什么促使您在凝聚态物理中探索拓扑学的应用?
A3:坦率的说,起初我甚至不了解拓扑学是什么。我只是隐约知道它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如何描述各种形状。直到我完成了大量计算,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关键作用。 随后我与David Thouless讨论,他指出这些涡旋本质上就是一种拓扑激发——就这样,“拓扑物理”登场了。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研究的本质,因为我真正关注并理解的是物理本身。我们将这些炫酷的数学概念引入物理领域,但最核心、最根本的始终是物理。
Q4:在您的理论突破之后,许多实验验证是在随后几年进行的,这些验证的时间线符合您的预期吗?
A4: 理论工作完成后,我们非常期待实验验证。当时有几个实验组在研究氦薄膜,特别是康奈尔大学John Reppy团队长期研究超流薄膜。所以我去康奈尔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有一天,我在研讨会报告我和David Thouless所取得的成果,但几乎没人理解我们的推理。我记得当时Kenneth G. Wilson(198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在场,他问了我一个不甚相关的问题,我只能支吾以对。但当时有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完全听懂了我的研究:David R. Nelson(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从那时起,我们科研合作得非常融洽。
所以当时,我们所做的涉及新物理,甚至被认为是异端思想,但结果证明它是对的。从想法提出到被验证,确实需要年轻开放的思想去理解和发展。后来,David R. Nelson和我进一步研究了归一化的超流密度。我们发现超流密度是一个与氦原子质量、普朗克常数等基本属性相关的普适常数。作为液体的刚度常数,超流密度在本质上是实验可测量的,完全可以通过流动的性质进行表征。
当然,超流性意味着流动中没有耗散,暗示流速是有限的。然而,理论预言是在零流速下成立的,需要从动力学预言进行外推,才能与所有的实验测量完美吻合。这项工作后来由David R. Nelson、维奈·安贝加卡(Vinay Ambegaokar) 和B·I·哈尔珀林(B.I. Halperin) 完成了。物理学界花了几年时间才接受这个奇怪的理论(KT相变)是正确的。
Q5: KT相变已在超导性、超流性和二维材料等领域得到应用,您如何看待这些应用?
A5:在超导性及相关现象的应用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说超导体也是一种超流体,我们的理论也应该适用于它。涡旋是超流体中需要考虑的基本激发,涡旋核在二维中可以描述为点粒子,其相互作用如同库仑相互作用。你可以用同样的涡旋语言来描述超导性,只是超导薄膜中的涡旋相互作用是带有有限屏蔽长度的屏蔽库仑相互作用。
David Thouless和我发表过一篇论文,预言超导薄膜中不应发生相变。但事实证明,超导薄膜的穿透深度通常非常长——甚至比实验系统本身还大。因此,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超流体理论也能适用于某些超导薄膜。同样地,对于穿透深度大于其某一维度的二维材料,KT相变也可以应用。David Thouless基于拓扑思想提出了各种美妙的应用。唯一令人沮丧的是,我当时身体出了点问题,导致我大约有半年时间无法参与工作。自那以后,KT相变已在各种系统中,包括量子和经典系统,都找到了广泛的应用。
Q6:拓扑概念如今在物理学中被广泛应用,引领了量子计算等应用,您对此有何看法?
A6:在将拓扑思想引入物理学方面,David Thouless的贡献更为卓著。但既然我也参与其中,我的名字也与之相关联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在量子计算中,你需要某种载体来存储和处理信息,而拓扑材料在这方面具有关键优势,因为它是非局域的:它们会扩散,因此不易受局部缺陷的影响,而这在普通材料中是不可避免的。
Q7: 您能列举出凝聚态物理学中三个最重要的未解问题吗?
A7: 预言并非我的强项,我更倾向于在探索中寻找重要问题。对我而言,当前一个重要的未解问题存在于非平衡系统。对于任何一个非平衡态的系统,在数学上一定存在无数的解,即稳态。那么其中某一个稳态是独一无二的?要探究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在系统中引入随机噪声并观察其演化。系统最终弛豫到的稳态,是否是唯一的、确定的?还是依赖于初始条件?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与生命本身的演化过程直接相关。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这都不能算是个问题,然而对我而言,这是终极之问,再无其他问题能与之比肩。
Q8:《eLight》旨在拓展光学边界并探索跨学科研究。而您将拓扑学应用于物理学,展示了打破学科边界的典范。在探索跨学科研究时,最应该重视什么?什么样的跨学科研究能产生广泛影响?
A8:我思考过这类问题——但老实说,我并没有标准答案。现实情况是,许多重大发现往往不期而至。一些看似奇怪甚至荒谬的想法,最终可能被证明是关键且正确的。我不相信有人能预言哪个特定领域或交叉会诞生重要的想法——它可能在任何地方涌现。因此,做研究时不必刻意追求广泛影响。回想我研究KT相变时,目标绝非赢得诺贝尔奖。我研究它,仅仅因为它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想象一下,每天早晨醒来宣布‘今天我要做点配得上诺贝尔奖的事’,这固然不错,但这并不是科学的本质。你无法预知什么是重要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攻克一个真正令你着迷的问题。去享受探索的过程,幸运的话,你的工作自然会变得重要,并在更广阔的领域找到应用。
跨学科当然至关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要努力让你的工作被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所理解。David R. Nelson就理解了我的理论并着手设计实验,我亲眼见证了许多我从未设想过的实验得以实现。跨学科的精髓在于促进理论学家与实验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共同揭示真相。无论你的理论多么精妙,最终的试金石都在于:你的理论能否经受实验的检验。
Q9:回顾过去,在早期遭遇质疑时,是否有关键的时刻或洞见帮助您坚持自己的研究?
A9: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特定的想法或念头——而是遇到对的人合作,找到对的问题去研究。关于克服质疑,我个人的建议是:找一个真正让你兴奋的问题。一旦你为之兴奋,内生动力将支撑你克服重重困难。只要你的工作扎实且正确,质疑的声音终将消散。另一个关键是享受研究的乐趣。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通常你所热衷的课题,未必是资助方(付钱支持你研究的人)所看重的。许多人将“成功”置于“乐趣”之上,但一个不幸的事实是,真正能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凤毛麟角。因此,放下压力,不再强求功名,至关重要。
相反,专注于寻找一个令你着迷的问题,然后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必过分担忧他人的看法。如果幸运的话,这个问题可能被认为很重要。而且,我深信,如果你真正享受研究的乐趣,你取得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Q10:您对理论物理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有什么建议?
A10:我一直深感幸运,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知名学者(注:Hans Walter Kosterlitz,著名生物化学家,内啡肽的主要发现者之一)。 他才华横溢,思想充满非传统甚至离经叛道的色彩。他意志坚定,深信自己的研究既重要又值得深入探索。这种态度深刻地塑造了我,使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致力于理解事物的本质。正如贯穿我们整个对话的核心精神,我对年轻一代最真挚的建议便是:享受科研的乐趣。 科学家并非最富有的职业;但对我而言,科学家何其有幸——得以获得报酬,去享受探索科学的快乐。(来源:中国光学微信公众号)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86/s43593-025-00090-0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