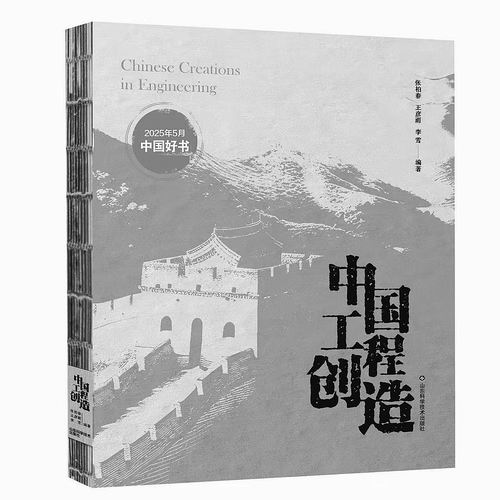 《中国工程创造》,张柏春、王彦雨、李雪编著
《中国工程创造》,张柏春、王彦雨、李雪编著
?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梳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多以“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两大类别对其进行划分。然而,像大运河这样的大规模创举——以天然河湖和人工河渠为核心,涉及地理、水利和造船等多个领域,究竟该归入“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发明”呢?
“显然都不太合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柏春指出,这是一项集地理勘测、水利开发、土木工程、漕运调度与国家治理于一体的系统性创造。在这种对科技活动与成就的分类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仅以二分法进行梳理,一些包括大运河在内的重大工程的归类就会面临困境。
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之外,或许还可以将“工程创造”作为第三类科技贡献,来系统研究和阐述中国的科技知识传统。基于这一想法,张柏春等编著的《中国工程创造》一书于2025年4月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我国古代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创造性的36项大国工程。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与张柏春的对话。
第三类科技贡献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意识到“工程创造”是与“科学”“技术”不同的第三类科技贡献形式的?
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些年编过一本《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这本书遴选出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共88项。在遴选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长城、大运河、郑和航海等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某种技术发明,而是内涵更宽的工程。于是,我们将88项古代科技成就细分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创造三类,这样比较合理。
科学发现与创造旨在发现和揭示自然的本质和规律;技术发明则旨在提出新的方法、器具、技能和工艺过程;而工程创造是指运用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创造性地将自然资源最适宜地转化为符合人类各种用途的物质实践活动。
《中国科学报》:过去我们讨论较多的是“不能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很少关注到技术与工程也容易被混为一谈。请你具体阐释一下工程是什么,它和科学、技术关系如何,三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张柏春:工程本质上是一种造物的实践活动,其核心在于通过运筹、决策、规划、设计、实施与管理等一系列系统性活动,将技术手段和科学原理整合运用于具体项目之中,最终创造出满足人类需求的人工系统或产品。
工程与科学和技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科学追求普遍性真理,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技术侧重于方法与工具的发明与改进,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工程则要在资源、空间、时间、安全、成本等多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实现特定目标的创造活动,关注的是“如何可靠、高效地造出来”。
工程不追求抽象的真理或单一技术突破,而是强调在现实条件下实现具体的目标。每一个工程实践都具有情境的独特性或唯一性。科学家的使命在于认知世界,其价值在于发现;而工程师的职责在于改造世界,其成就在于实现。工程师的工作是在已有技术和知识的基础上,面对复杂的实际条件,优先选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和方案,仅在必要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以确保整体系统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36项中国古今重大工程
《中国科学报》:《中国工程创造》展示了36项中国古今重大工程,选取的标准是什么?
张柏春:这36项工程中,古代工程共16项,包含了体现中国古代高超矿冶工程的铜绿山古铜矿、沟通南北水路交通的大运河、反映宋元时期技术水平的水运仪象台、应县木塔,以及我国古代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丝织和制瓷等。
近现代工程仅1项。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工程事业在社会动荡和战乱中艰难展开,因此仅选京张铁路1项作为代表。
距离我们较近的现当代工程共19项。其中,“两弹一星”工程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大基础设施极大提升了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中国天眼、载人航天等工程则为科技探索提供了先进手段,彰显了中国创造新知识的力量。
实际上,工程早已成为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值得大书特书。不过,限于篇幅,我们仅挑选36项,遴选的目标并非追求全面,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希望达到“窥一斑可知全豹”的效果。
《中国科学报》:书中图胜于文,有大量精美的图片资料而文字量很少,这是如何考量的?
张柏春:“用好看的图片说话”是我们的基本考虑。本书采用16开铜版纸、200余页的篇幅展示36项工程的概貌,其中每项工程用短小精悍的文字开篇,配以高清大场景照片及必要的示意图或地图等,力求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中国工程的魅力。
“厚图薄文”的形式也顺应了当下的阅读节奏。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可以提升阅读的趣味性,也让不同背景的读者能够以轻松、愉悦的心态走进工程世界。
工程因人而兴
《中国科学报》:是不是每一项工程中都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
张柏春:在许多重大工程的背后,常常有一位或多位灵魂人物,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例如,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设计“人”字形线路,巧妙化解八达岭隧道施工的高坡度难题,开创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之先河。放眼世界,有诸如主持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冯·布劳恩、推动苏联航天发展的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等工程领袖。他们不仅是技术领导者,更是工程理念和方向的设计者。
但必须指出,任何一项伟大工程的实现,都不是个人的成果,而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即使是总设计师,也依赖由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乃至管理者构成的庞大团队的共同努力。
《中国科学报》:相较科学发现而言,中国人在技术发明和工程创造上的表现似乎更突出一些?
张柏春:是的。中国科学家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缺少诺奖级的科学发现。中国专利数量大幅增加,但缺乏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重大发明。中国人在工程方面取得了遍地开花的业绩,也在创造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工程中,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各种社会需求。
总之,中国是工程大国,也是工程强国。造物是中国人的禀赋!
中国人有高超的工程运筹、组织和实施能力,在实践中强调集体协作、吃苦耐劳,能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展开快节奏的工作。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工程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人还有很强的学习和集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现代中国的早期工程实践带有“模仿”色彩,但能够将“模仿”与国情相结合,使得舶来的技术本土化。如今,中国人更加追求创新,力争获得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工程领域不断创造佳绩。
《中国科学报》(2025-09-05 第3版 读书)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