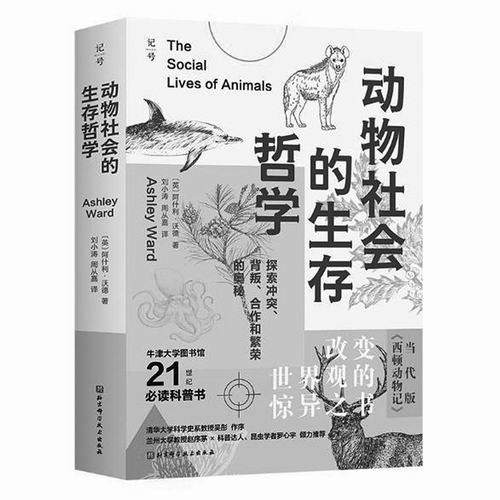 《动物社会的生存哲学:探索冲突、背叛、合作和繁荣的奥秘》,[英]阿什利·沃德著,刘小涛、周从嘉译
《动物社会的生存哲学:探索冲突、背叛、合作和繁荣的奥秘》,[英]阿什利·沃德著,刘小涛、周从嘉译
?
■ 吴彤
刘小涛的动物行为研究译作,这是第四部了。第一部是康拉德·洛伦茨的《论攻击》(与何朝安合作),第二部是尼可拉斯·廷伯根的《动物的社会行为》,第三部是马克·贝科夫等的《野兽正义:动物的道德生活》。现在是第四部,译自阿什利·沃德的《动物社会的生存哲学:探索冲突、背叛、合作和繁荣的奥秘》。通过译介与研究,小涛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动物行为哲学的研究者。这是值得赞赏的事,因为国内相关研究的从业者太少,希望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坚持下去。
本书关于动物合作应对自然的讨论,基于大量具体的观察和有趣的动物行为故事。这些有趣的观察表明,动物界的合作在不同物种中具有多样性、地方性特征,不能一概而论。本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讨论了合作的价值,而且告诉读者,合作在动物界是具有多样性的。考察动物的合作,需要深入某个物种中,进行具体且细致的研究。
合作,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的
最开始,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动物合作:吸血蝙蝠互相帮助的故事。如果有只蝙蝠饿着肚子回来,另一只饱餐鲜血的蝙蝠会过来提供帮助,就像鸟妈妈给巢里的幼鸟喂食,成功的蝙蝠猎手会让一些鲜血从胃里反流出来,慷慨地喂给它那不走运的同伴。
作者指出,类似这样的合作,是社会动物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像蝙蝠这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模式并不普遍,但几乎所有群体生活的动物都会给同伴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在最基本的水平上,这可能表现了社会缓冲与合作的一种形式。特别紧要的是,这可能意味着,从磷虾到人类的社会动物,仅仅因为与同伴的相处或互动,就能从中获益。
对人类而言,和他人一起生活还有许多更深远的影响,比如语言能力的发展,以及日常与人相处的方式。这甚至是人类智能进化的基础,而智能通常被视为人类的标志。最终,我们的合作本能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其实,这一本能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的,它是我们从人类和动物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内在特征。
在动物王国,许多动物利用社会性来解决生计问题。群体生活为许多生物的成功生存提供了平台。而且,在人类社会和其他一些动物社会之间,我们能发现直接且重要的相似结构。这些相似的平行结构反映了我们的进化之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究竟社会性在多么基础的层面上塑造了我们的生活。通过更好地理解动物,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
作者指出,群体和合作常常是进步的基础,也是有意义的生活的基础。
作者还讨论了动物与人类社会的谱系关系。现代人类社会由家庭、团体、城市和国家构成,体现了复杂的文化、习俗、关系、法律等特征。从这些方面考虑,似乎人类社会和其他动物迥然不同。然而,作者特别指出,虽然人类社会有许多独有的特征,但其组织方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许多社会动物用相似的方式进行组织,它们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这么做了。
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其自身的认知价值,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进化基础。
互惠的合作关系
“社会性”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出于此书目的,作者这样定义社会动物:它们依赖同类,和同类一起生活、互动。而动物的社会性就是:它们之间有何种联系;它们怎样在竞争关系中形成合谋,又怎样结成同盟并相互合作。
为了论证这些观察,作者讨论了类型多样的动物合作:从磷虾这类低等的没有“脸”的生物的合作,一直到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合作,都在本书的覆盖范围以内。让我们先看看磷虾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它们又是如何合作的。
磷虾是南大洋的基石物种。从企鹅到信天翁,从海豹到鲸,磷虾都是它们食谱上的首选。如果磷虾消失了的话,显然,相当多的其他珍贵南极物种也会随之消失。
磷虾展示出所有社会动物(包括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们不喜欢独处。磷虾在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我们甚至能看到它们搏动的小心脏。从群体中隔离出来,它们心脏的跳动会加快。它们对危险的反应之快令人惊讶。检测到危险信号后,它们只需要50~60毫秒就能做出逃避反应。磷虾是许多掠食动物的盘中餐,面对相当多的掠食动物,大规模聚集能为磷虾提供较好的保护。
而面对无数旋转跳动着的南极磷虾,那些需要一只一只挑拣受害者的掠食动物(绝大多数掠食动物都如此),会因视觉超负荷的问题,而导致挑选困难——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小型甲壳纲动物还有其他一两个可用的花招。根据报道,有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掠食动物,比如一条鱼或一只企鹅,磷虾会自主褪下虾壳。期待胜利时刻的掠食者,被空空如也的虾壳吸引,而磷虾则逃之夭夭了。
许多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都有类似互惠的合作关系,而不只是捕食与被捕食的竞争关系。比如,鲸和磷虾在生态系统中就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方的成功也有益于另一方。鲸的粪便富含铁、磷、氮等营养成分,对磷虾爱吃的一些浮游植物来说,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些浮游植物也为磷虾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食物。
个体与集体
蝗虫有另一种社会性合作方式。和南极的集聚磷虾群不同——磷虾群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蝗虫的爆发则是地域昆虫生态危机的周期性表现。研究表明,蝗虫有两种不同的形态,或称生态相。处于独居相的蝗虫,就像隐士一般,避免与同类接触,危害也相对较小。只有当它们进入群居相的时候,才会出现聚集并且造成生态灾难。
是什么原因促使蝗虫从相对无害的独居相转变为抢劫团伙的成员?科学家发现,蝗虫之间的身体摩擦,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蝗虫后腿在刺激的作用下释放大量血清素,它们流向蝗虫的身体,让蝗虫发生180度的大改变,从独居隐士变为热衷聚会的一员。
血清素是一种和降低攻击性、促进社会行为相关联的神经递质。对蝗虫而言,血清素的增加会激发蝗虫身体的一系列变化。从孤僻隐士到热衷社交的改变最为明显,紧接着发生的系统性重塑,让蝗虫完全变身为羽翼丰满、贪得无厌的庄稼破坏者。这时,它们的同类也成为食谱上的食物,因此它们必须一直向前,否则就会被后面的同类吃掉。所以,蝗虫向群居性的第二自我转变,乃是应对死于饥饿的紧急措施;蝗虫群的大规模移动,则是一场强制性的“急行军”。
另外,如果雌性蝗虫一开始就生活在密集的蝗虫群里,产卵的时候,它就会给卵涂上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会让它的后代直接发育成群居相,而不需要经历麻烦的摩擦大腿的过程(它们的母亲或许经历过这个过程)。这种行为有个突出效应:一旦蝗虫群的聚集开始形成,群居相蝗虫就获得了自发的动力,能够将聚集行为直接向下一代传递。这就是驱散一个蝗虫群非常困难的原因。
作者还讨论了讨厌的蟑螂。蟑螂也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作者后面花费了更多笔墨描述、讨论和研究了蚂蚁(各种蚂蚁)、黄蜂、白蚁(如白蚁的战斗、合作与蚁穴的建造),它们常被人们称作社会性昆虫。它们是紧密联系的集体,每个个体都为集体的成功作出贡献,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集体赢得更大利益。
对许多蜂来讲,在相互合作的巨大群体里生活是它们颇为成功的策略。问题是,这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昆虫牺牲自己的个性特征,甚至繁殖机会,而听任命运的安排,甘愿承担照顾“别人的小孩”这种更次要些的工作呢?蜂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本书揭示了这个物种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包括独居蜂和群居蜂的差异。蜂仍然可以从“整体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中获益。整体适应性指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能将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适应性。
社会性昆虫是地球上最令人着迷的动物。它们和我们差异巨大,然而,它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显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像我们一样,它们也是“农民”和“建筑工人”,努力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它们也保卫自己的动物社会这一生存哲学家园,还会进行专门的分工。除人类以外,只有它们能举数百万之众形成组织严密的社会。它们还具有某些人类的不良特征,包括剥削奴隶,这个相似之处颇让人吃惊。
另外还有鸟群。包括椋鸟的群集现象、鸟群的V形飞行,等等。鸟类的群体导航偏好也是合作的极好例子。虽然每只鸟对飞行方向的偏好略有不同,但只要聚在一起,鸟群作为一个整体就能从某些难以置信的、精确的集体导航中获益。
合作还使得社会性学习得以延续和发展。比如,人们观察到山雀会偷食城市中送奶工所送牛奶顶部的奶油,而其他山雀很快就学习到这项技能。
从独立生存过渡到群体生活
作者关于动物界合作的叙述都是故事性的。每种动物特有的合作方式和行为,都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这使得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没有教科书般说教的沉闷和刻板。译作配图若干,更有可读性,更加吸引读者。
对我来说,此书的一些评论也富于启发。比如,作者曾论及交游很广、和朋友保持良好关系,这些因素甚至比体育锻炼更易于让人获得健康、高质量的老年生活。我在生病期间对此体会尤为深刻。本书还破除了一些成见,比如,“群体思维”“从众心理”和“随大流”这样的词曾被认为是极其消极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社会交往的潜意识规则非常有益。例如,每当我们走过拥挤的人行横道时,我们就会排成一队,跟在和我们方向相同的人后面过马路,否则就可能会带来问题。
从个体的独立生存过渡到群体生活,这是地球生命史最为重要的进化;深刻而具体地揭示出这一点,或许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人类也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特点。我们的生活总是离不开家庭和朋友。近些年的社会经验,不管是社会帮助,还是社会隔离,似乎都使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除了智能、语言、长寿、意识、推理、社会学习和文化,社会性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也许,我们应和作者一样,在理智上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
(本文为推荐序,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