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龙泉学校的孩子们在“阳光校厕”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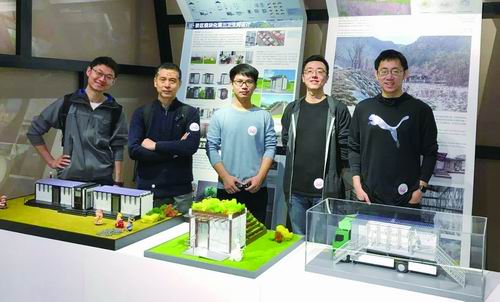
▲刘新(左二)、梁骥(左一)与生态厕所设计团队成员。受访者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蒲雅杰
“厕所又‘脏’又‘low(低级)’,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地搞设计?”
“一群小姑娘、小伙子去农村设计厕所,以后还能找到对象吗?”
2015年,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下简称清华美院)教授刘新带着学生一头扎进“生态厕所建设”实践时,质疑的声音不时响起。有人说他们是“专管上厕所的设计师”,也有人不解:清华美院的大雅之堂,怎么研究起了解决大小便的问题?
那时的刘新总说:“很值得。”
得益于这样的坚持,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厕所、西部农村地区的旱厕等,经过他们设计后拥有了更安全、更合理的如厕方式。
在清华,刘新将“生态厕所设计”作为核心案例搬上了名为“可持续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生选修课。虽然这只是一门小班课程,却年年报名火爆。
然而坚持久了,他也开始有些疲惫。“这几年,风向变了,改厕项目经费和投资不断缩减,继续做下去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刘新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从不强求学生们毕业后继续从事改厕事业。相反,他只是说:“设计师要有理想,但也该先考虑生存。”
如今,这些年轻人有的还在坚守生态厕所设计,有的则进入了知名车企,有的投身智能硬件,有的创业做起了家居品牌。无论如何,在刘新10年间身体力行的感召下,他们心中期望改变乡村、改造世界的人文关怀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之火从未熄灭。
结缘
与厕所“绑定”,对于刘新而言是一个偶然却又必然的过程。
1987年,刘新自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现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毕业后,入职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一待就是7年。
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他所设计的并非仅供展示的概念车型,而是要真正驶上道路、经受日常磨损的实用交通工具。20世纪90年代后期,刘新转型成为自由设计师,穿梭于企业与市场之间,协助企业解决产品从图纸到量产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中便包括卫浴洁具的设计开发。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自己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对真实生活需求的回应”。
深受彼时全球可持续设计思潮的影响,2006年,获得清华美院工业设计系博士学位的他留校任教。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产品设计之间,找到一个培养学生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落脚点,成为他这一时期探索的主旋律。
而这个落脚点出现在2014年。这一年,他以中国工业设计专家的身份,受邀担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厕所创新大赛”项目中国地区的评审委员。起初他有些不解,一个以推动尖端科技著称的富豪,为何会把厕所和核能、生物医药并列为重点项目?
随着对此话题的了解日益深入,答案逐渐清晰。比尔·盖茨认为,厕所是关乎人类生存尊严的“尖端民生工程”,在非洲等地区,无数儿童因粪便污染导致的腹泻而夭折。因此,盖茨号召全球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技术创新,打造一种无需下水道、不依赖电网、能低成本将粪尿就地处理的新型厕所系统。
作为在北京胡同中长大的孩子,刘新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自幼不堪忍受的胡同旱厕:“夏天臭、冬天冻,直到‘满载’后再由淘粪工人清理,条件非常简陋。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胡同才逐渐有了暖气、冲水式厕所,但卫生状况仍不理想。”
从实际经历出发,一项将工业设计教学与“改厕革命”相结合的实践计划,逐步在他心中酝酿。2015年,在刘新的牵头下,由工业设计、生态农业、环境设计、社会创新专业师生组成的厕所研究与设计项目组正式成立。
区别于盖茨强调对厕所后端的“绝对净化”路径,刘新认为,在中国,厕所设计有着独特的现实语境。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卫浴产业发达,陶瓷、洁具产能巨大,但多集中于城市中高端市场;而农村和老旧城区的旱厕、简厕改造,仍缺乏系统性设计的介入。因此,团队尝试先从前端破题,为中国不同地区的如厕窘境提供解决方案。
“破题的第一步,必须是三个字——挨个试。”刘新说。
在他看来,真正的设计,不仅只服务高端人群与艺术,更要服务普罗大众与社会。后来的10年里,从北京东城区胡同中老旧的公厕,到64个地势崎岖、气候恶劣的村庄旱厕,他们先考察试用、再设计改造,脚步未曾停歇。
“这不是拍一张照片就能感同身受设计出的成果,只有亲身体验过其中的痛点,才有资格触摸到真实的需求。”他时常对学生强调。
解困
“你认为,最好的厕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可持续设计理论与实践”课上,刘新总会向台下的学生抛出这个问题。对于厕所这个“隐秘的角落”,很少有人会特别关注,因此教室里总有片刻沉默——有人低头笑,有人迟疑举手:“又香又干净,还配备了最智能的马桶?”
而刘新不急于回答,只是引导学生去思考:在高原缺水的村落,冲水是一种奢侈;在高寒地带,管道容易冻结;在城市老旧小区,空间逼仄,排污改造寸步难行……“如果设计只服务于已拥有宜居生活的人,那它还称得上‘设计’吗?”
话外,他更想说的是,一个简单的厕所,却是一些人难以言说的“心病”。改厕,更像是在“治病”。
“在西北的农村,人们基本用水都捉襟见肘,又怎么能奢望用它来冲刷厕所?”博士研究生梁骥坦言。有团队成员告诉他,自己每次试用老乡家的旱厕前都要“做一万次心理建设”,因此非常理解他们为何将洗菜的水留下来洗衣服。在刚通自来水的黄土高原,对于水的珍视已经融入当地村民的生活。
2015年,“90后”的梁骥刚从交通运输这一工科专业跨界工业设计领域,进入项目组实习。在团队的影响下,他一头扎进了厕所改造工作,一干就是10年。
一支笔、一个本,一张小木桌,大爷、大妈曾围着他说出旱厕的诸多问题:夏天臭气熏天,苍蝇成群;冬天寒风刺骨,地面结冰,老人颤巍巍地扶着墙进出,稍有不慎就可能摔倒;更难的是,清淘一次要花几百元,还常常找不到人来干……这些现实问题像一堵墙立在他面前,也成了他研究的起点。
“许多家庭并非不愿改厕,但现有的方案要么耗水太多,不现实;要么成本太高,用不起;要么维护复杂,没人管。”刘新告诉梁骥,解决设计难题不在于运用高端、先进的技术,而是如何在资源极度受限的条件下,做出安全、实用、易维护的产品。
2019年,在刘新的指导下,项目组设计出了一款“免水冲蹲坐一体便器”。它采用高密度泡沫材料座圈,冬天坐着不冰凉,解决了“冻屁股”的尴尬。这款便器没有上下水连接,彻底摆脱了对水资源的依赖。其内部通过巧妙的隔板结构实现粪尿分离——尿液经简单稀释即可作为液态肥还田,粪便则进入发酵仓。
发酵仓中,粪便经过一段时间的微生物处理,转化为稳定、无臭的土壤改良剂,真正实现“变废为宝”。这些生物菌由团队与微生物专家合作筛选,他们根据菌种特性及不同地区的使用条件,确定菌剂与菌粉的处理方式。
据梁骥回忆,“免水冲蹲坐一体便器”最初在偏远地区进行推广时,一度无人问津。
事实上,改厕经费大多由地方政府承担,有的全额补贴,有的让村民出一点水泥、沙子的钱,大约两三百元,而个别地区村民则需承担五六百元。“费用再高,村民就摇头了。”梁骥说道。
资金是一关,观念更是无形的障碍。一些长期使用旱厕的老人担心损坏新厕所,仍然坚持使用旧旱厕,不愿跨出改变如厕方式的第一步。
面对推广的困境,梁骥灵机一动,写了条横幅挂在村口,“厕所改得好,娃娃过年回家早;厕所改得好,孙子住到闹元宵”。
这是因为梁骥发现,在不少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和空巢家庭居多,每逢佳节,习惯了城市里冲水马桶的年轻人,早已无法适应简陋的茅厕。“建个新厕所,留孩子们多住几天,就是老人们最朴实的心愿。”梁骥说。
以感情需求为抓手,再在村民们耳边“吹吹风”,很快,新型厕所便有了销路。
“免水冲蹲坐一体便器”近年来获得了包括日本优良设计大奖、德国IF设计大奖、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等国内外众多设计奖项。2021年,中国可持续设计大奖评审之一Aric Chen盛赞道:“它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决了一个严重的、大规模的问题……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功能、健康、成本、实用性方面,关注了用户的需求、习惯和当地文化。”
在后来的回访中,团队成员们欣喜地发现,从“要我改”到“我要改”,老乡们开始自发维护如厕条件,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截至目前,新型生态厕所已惠及中西部地区近万户农村家庭。
求生
2015年,我国从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入手,正式启动“厕所革命”,强调“小厕所、大民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厕所研究与设计项目组应运而生,并在成立初期便与政府部门合作,投身于北京东城区胡同公厕以及部分景区老旧厕所的改造实践。
“除了政府委托之外,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可以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进行。”刘新说。
2020年,团队注意到,清华大学每年都会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西北地区的支教项目。团队萌生了一个想法:为那里的孩子们建一座厕所。经过积极沟通,他们最终获得一家企业的爱心支持,成立“阳光校厕”公益计划,由此启动了一场难忘的改厕之旅。
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龙泉学校,由于高、寒、旱的贫瘠环境,1000多名师生长期没有厕所可用。调研过程中,一些住校的孩子说,他们晚上不敢喝水,就怕上厕所。“由于生理结构不同,男生尚可将就,女孩尤其困难——她们每天都在忍耐和克制,甚至会因此焦虑,进而影响学业。”
如今已毕业的硕士生梁同学记得,当走进那间黑漆漆的旱厕,打开手机灯光,浓烈的气味和肮脏的景象使她眼泪狂飙。她说自己那时“跑出来马上就吐了,一边哭一边吐”。
改造,势在必行。对此,团队设计了一款集装箱式厕所,并在建筑师的协作下搭建在学校的一角。在每个隔间中,他们还设计了一套适合高寒环境的如厕设备,提供专用的男生小便厕间,并将更多的空间作为男女通用厕间,优先供女孩使用。
“一年后,当我们回访时,发现厕所保持得非常干净,老师说娃娃们终于可以随便喝水了。”那次项目让刘新深刻体会到,厕所不只是基础设施,还是尊严、健康,乃至教育公平的保障。自己的这条路“走对了”。
然而,像“阳光校厕”这样的公益赞助并不多见,很多时候,一些优秀的生态厕所设计只能“明珠蒙尘”,停留在图纸与模型阶段。
2023年,刘新和团队在西藏的高原深处,关注到一种古老的如厕方式——人们在传统藏式建筑二层房间外悬建一间木屋,排泄物直接落入下方的深坑或荒地。
如何为他们量身打造更卫生、更环保的厕所?团队没有照搬城市的冲水模式,而是在尊重当地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融合传统与生态技术的新型旱厕:将厕所建在吊脚楼结构上,底部预留空间用于堆肥。每次使用后,使用者只需踩动踏板,侧仓便会撒下一小撮混合垫料,这些垫料由牦牛粪灰、青稞壳和本地生物菌种调配而成,形成“生态覆盖层”。一脚踩下去,不仅完成了掩埋,也启动了自然降解过程。
“很可惜的是,尽管方案获得了许多设计专业同行的认可,却没有企业提供赞助让成果落地。”刘新叹了口气。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高原项目维护成本高、市场回报慢,商业资本望而却步也合乎情理,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将立刻推出成熟且适配的产品。
现实的困境远不止于此。刘新深切感受到,整个行业的风向是收紧相关项目并压缩预算,甚至搁置;企业也对研发投资愈发谨慎,宁可观望也不愿承担风险。
“厕所这事儿,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梁骥说,“上游断‘水’,下游断‘粮’,到了我们设计端,只能凭一腔信念守候了。”
信念不能当饭吃,设计也不能只靠情怀落地。面对经费的困局,他们开始摸索一条“求生”之路。
清华大学的校内资源与支持,为团队设计作品提供了前期基础试制和研发费用,是他们的坚实后盾。同时,各类设计大奖及竞赛,也成了他们重要的突破口。“一个亮眼的方案,不仅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还是发声宣传的渠道,促成了很多试点项目。”梁骥说道。
前不久,2025年戴森设计大奖中国大陆赛区奖项正式揭晓。梁骥与师弟黄俊铭带着他们的设计作品“Pureco免水冲生态户厕系统”夺得冠军,并赢得全球20强席位。这款厕所像一间“万能小屋”,如厕后无需水电接入,仅利用太阳能集热与被动保温技术,就能实现粪尿的无害化、减量化与资源化处理。
“我们的设计,每年可为农户节省维护成本超300元。更关键的是,它通过助便踏板、防滑扶手等人性化细节,提升了如厕的安全与舒适度。”黄俊铭介绍道。
梁骥表示,未来他们将尝试面向终端消费者,将生态厕所技术应用于有机农场、精品民宿、文旅营地等对环保和体验有更高要求的空间。
“尽善尽美,尽力而为。”谈及10年来的体会,刘新说,“生态厕所设计只是其中一个选题,而我们始终没有偏离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主线。”
作为中国可持续设计学习网络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刘新带领着生态设计研究团队长期耕耘于可持续设计领域。在他们的努力下,新颖的设计创意不断涌现:集废料处理与有机种植于一体的“生菜屋”可持续生活实验室、利用海浪能量助力的近岸垃圾收集设备、以丝瓜络纤维材料制成的人体矫形仪,以及居民参与式社区花园共建……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人、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共进。面对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无论前路多么漫长,设计师都应怀揣改变世界的理想。”刘新说,“而能将这个理想付诸实践的人,是幸福的。”
《中国科学报》(2025-10-14第4版高教聚焦)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