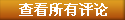|
|
|
|
|
иҜ»и·ҜйҒҘпјҡе№іеҮЎзҡ„дё–з•ҢдёҚе№іеҮЎзҡ„дәә |
|
|

гҖҠж—©жҷЁд»ҺдёӯеҚҲејҖе§ӢгҖӢпјҢи·ҜйҒҘи‘—пјҢеҢ—дә¬еҚҒжңҲж–ҮиүәеҮәзүҲзӨҫ2012е№ҙ4жңҲеҮәзүҲ
в– жҙӘзғӣ
1992е№ҙ11жңҲ17ж—ҘпјҢдҪң家и·ҜйҒҘеңЁиҘҝе®үеӣ з—…еҢ»жІ»ж— ж•ҲзҰ»дё–пјҢе№ҙд»…42еІҒгҖӮ20дё–зәӘ80е№ҙд»ЈпјҢд»–д»ҘеҲ»з”»й»„еңҹй«ҳеқЎзҡ„йҷ•еҢ—дәәжІүйҮҚе‘Ҫиҝҗзҡ„е°ҸиҜҙгҖҠдәәз”ҹгҖӢе’ҢгҖҠе№іеҮЎзҡ„дё–з•ҢгҖӢеңЁе…ЁеӣҪеј•иө·е·ЁеӨ§еҸҚе“ҚпјҢеҪұе“ҚдәҶдёҖд»Јдәәзҡ„жҲҗй•ҝ……
жҲ‘зҡ„ж•Јж–ҮжӣҫиҺ·1997е№ҙ第еӣӣеұҠзҡ„“и·ҜйҒҘйқ’е№ҙж–ҮеӯҰеӨ§еҘ–”гҖӮжҲ‘жүҖеңЁзҡ„дёӯеӣҪж–ҮиҒ”еҮәзүҲзӨҫжҺЁеҮәзҡ„гҖҠе№іеҮЎзҡ„дё–з•ҢгҖӢиҺ·иҢ…зӣҫж–ҮеӯҰеҘ–гҖӮ然иҖҢпјҢзӣҙеҲ°иҜ»и·ҜйҒҘгҖҠж—©жҷЁд»ҺдёӯеҚҲејҖе§ӢгҖӢпјҢжүҚзңҹжӯЈзҹҘйҒ“гҖҠе№іеҮЎзҡ„дё–з•ҢгҖӢжҳҜжҖҺд№ҲиҜһз”ҹзҡ„гҖӮ
дёҖеҲҮдјјд№ҺйғҪеҸ‘з”ҹеңЁдёҚд№…д»ҘеүҚпјҢеҸӨеҹҺиҘҝе®үзҡ„дёҖеә§з®ҖйҷӢжҲҝеұӢйҮҢпјҢжңүдҪҚйқўе®№жҶ”жӮҙзҡ„дёӯе№ҙз”·дәәеңЁжҳҸжҡ—зҡ„еӨ©иҠұжқҝдёӢжқҘеӣһиёұжӯҘпјҢеӨңдёҚжҲҗеҜҗгҖӮд»–иў«е·ІеҺҡз§ҜеҰӮе°ҳеңҹзҡ„дёҖдёӘж—©е№ҙжўҰжүҖе”ӨйҶ’гҖҒжүҖжҠҳзЈЁпјҡиҝҷдёҖз”ҹеҰӮжһңиҰҒеҶҷдёҖжң¬иҮӘе·ұж„ҹеҲ°и§„жЁЎжңҖеӨ§зҡ„д№ҰпјҢжҲ–иҖ…е№ІдёҖз”ҹдёӯжңҖйҮҚиҰҒзҡ„дёҖ件дәӢпјҢйӮЈдёҖе®ҡжҳҜеӣӣеҚҒеІҒд№ӢеүҚгҖӮз„ҰзҒјдёҚе®үзҡ„еҝғд»ҝдҪӣеңЁжңҚд»ҺеҶҘеҶҘд№Ӣдёӯзҡ„зҘһж—ЁпјҢд»–зҹҘйҒ“дёҠи·Ҝзҡ„ж—¶й—ҙеҲ°дәҶгҖӮдёҖзүҮиӢҚиҢ«еҜӮеҜҘзҡ„жІҷжј йҡҗзәҰжө®зҺ°дәҺзңјеүҚ——жҗәеёҰзқҖжІүеҮқеҰӮеӨ©зұҒзҡ„е‘је”ӨгҖӮдё–дҝ—з”ҹжҙ»зҡ„еҳҲжқӮдёҺзә·жү°йЎҝж—¶ж¶ҲеӨұдәҶпјҢдёӯе№ҙз”·дәәз®ҖзӣҙдёҖеҲҶй’ҹд№ҹдёҚж„ҝиҖҪжҗҒпјҢе°ұ收жӢҫиө·еЎһж»Ўж–№ж јзЁҝзәёе’ҢеңҶзҸ 笔иҠҜзҡ„иЎҢеӣҠпјҢи„ұзҰ»й’ўзӯӢж°ҙжіҘзҡ„еҹҺеёӮгҖӮ“жҲ‘еҜ№жІҷжј ——зЎ®еҲҮең°иҜҙпјҢеҜ№ж•…д№ЎжҜӣд№Ңзҙ йӮЈйҮҢзҡ„еӨ§жІҷжј жңүдёҖз§Қзү№ж®Ҡзҡ„ж„ҹжғ…жҲ–иҖ…иҜҙзү№ж®Ҡзҡ„зјҳеҲҶпјҢйӮЈжҳҜдёҖеқ—иҝӣиЎҢдәәз”ҹзҰ…жӮҹзҡ„еҮҖеңҹпјҢжҜҸеҪ“йқўдёҙе‘Ҫиҝҗзҡ„йҮҚеӨ§жҠүжӢ©пјҢе°Өе…¶жҳҜйқўдёҙз”ҹжҙ»е’ҢзІҫзҘһзҡ„дёҘйҮҚеҚұжңәж—¶пјҢжҲ‘йғҪдјҡдёҚз”ұиҮӘдё»ең°иө°еҗ‘жҜӣд№Ңзҙ еӨ§жІҷжј ……”
иҝҷдҪҚе№ҙеұҠдёҚжғ‘зҡ„з”·дәәеҗҚеҸ«и·ҜйҒҘпјҢдҝғдҪҝд»–жҠ•иә«иӣ®иҚ’жІҷжј е№¶дё”еңЁеҶ…еҝғеІ©жөҶиҲ¬жұ№ж¶ҢдёҚжҒҜзҡ„йӮЈдёӘжўҰпјҢжҲҗеҪўеҗҺиў«е‘ҪеҗҚдёәгҖҠе№іеҮЎзҡ„дё–з•ҢгҖӢгҖӮи°Ғд№ҹжғіиұЎдёҚеҲ°пјҢе№іеҮЎзҡ„дё–з•Ңеұ…然еңЁиҚ’ж— дәәзғҹзҡ„иҝңеӨ©иҝңең°йҮҢжӢүејҖеәҸ幕пјҢз”ҡиҮідҪңиҖ…жң¬иә«д№ҹдёҚеҫ—дёҚжңҚд»Һиҝҷе‘Ҫиҝҗзҡ„е®үжҺ’пјҢеӣ дёәйӮЈйҮҢ——д»…д»…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иҝҳеӣәжү§ең°дҝқз•ҷзқҖд»–з”ҹе‘Ҫзҡ„жҷЁжӣҰгҖӮж—©жҷЁд»ҺдёӯеҚҲејҖе§ӢпјҢдёӯе№ҙз”·дәәиөӨи„ҡиЎҢиҝӣеңЁиҢ«ж— ж¶Ҝйҷ…зҡ„йЈһжІҷиө°зҹід№ӢдёӯпјҢеҒ¶е°”еӣӣиӮўеӨ§еұ•еҚ§дәҺжІҷдёҳдёҠеҮқи§Ҷй«ҳж·ұиҺ«жөӢзҡ„иӢҚз©№пјҢеҜ№зҘһеңЈзҡ„еӨ§иҮӘ然充满иҷ”иҜҡзҡ„ж„ҹжҒ©д№Ӣжғ…гҖӮд»–еңЁеӨңй—ҙдёҖзҒҜеҰӮиұҶзҡ„еҲӣдҪңжүӢи®°йҮҢејәи°ғйҒ“пјҡ“е°Ҫз®ЎжҲ‘еӨҡе°‘ж¬ЎжқҘиҝҮиҝҷйҮҢжҺҘеҸ—зІҫзҘһзҡ„жІҗжөҙпјҢдҪҶжӯӨиЎҢж„Ҹд№үйқһеҗҢеҫҖеёё……еҶҚдёҖж¬Ўиә«дёҙе…¶еўғпјҢжҲ‘зҡ„еҝғжғ…д»ҚеғҸиҝҮеҺ»дёҖж ·жҝҖеҠЁгҖӮ”йӮЈжҜ•з«ҹжҳҜд»–и—•ж–ӯдёқиҝһзҡ„иҜһз”ҹд№Ӣең°пјҢд»–еңЁзҶҹзЁ”еҰӮйҡ”дё–йҮҚйҖўзҡ„ж°ӣеӣҙдёӯ“з”ЁеӨ§е®Үе®ҷзҡ„и§’еәҰжқҘи§Ӯз…§з”ҹе‘ҪпјҢи§Ӯз…§дәәзұ»зҡ„еҺҶеҸІе’ҢзҺ°е®һ”пјҢеҝғж— ж—ҒйӘӣ——зӣҙеҲ°ж··жІҢжңӘејҖзҡ„дҪңе“Ғдёӯжҹҗдәӣдәәзү©зҡ„иҪ®е»“жёҗжёҗеҮәзҺ°еңЁе№ҝйҳ”зҡ„ең°е№ізәҝдёҠгҖӮ
жҲ‘зҝ»ејҖең°еӣҫеҶҢпјҢеҚҙжҹҘжүҫдёҚеҲ°йҷ•иҘҝзҡ„жҜӣд№Ңзҙ жІҷжј ——е®ғеӨӘе°ҸдәҶгҖӮдҪҶеңЁи·ҜйҒҘеҝғзӣ®дёӯпјҢе®ғи¶ід»Ҙжһ„жҲҗж•ҙдёӘдё–з•Ңзҡ„жЁЎеһӢжҲ–жІҷзӣҳгҖӮдё–з•ҢжҳҜе№іеҮЎзҡ„пјҢз”ҹеӯҳеңЁдё–з•ҢдёҠзҡ„дәә们еҚҙжҳҜдјҹеӨ§зҡ„пјҢйӮЈзүҮйЈҺжІҷжј«еҚ·зҡ„ең°еҹҹе·ІжҲҗдёәи·ҜйҒҘзҒөйӯӮзҡ„еҪ’е®ҝпјҢдҪҶж—·дё–е·Ёи‘—гҖҠе№іеҮЎзҡ„дё–з•ҢгҖӢеҚҙдјҙйҡҸеҖ”ејәзҡ„й©јйҳҹиө°еҮәжІҷжј пјҢеҜ»жүҫеҲ°жҳҹиҫ°зҡ„дҪҚзҪ®гҖӮзҺ°еңЁпјҢе·Із»Ҹжңү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дәәзҹҘйҒ“дёҖеҗ‘еҜӮеҜһж— еҗҚзҡ„жҜӣд№Ңзҙ дәҶпјҢзҹҘйҒ“иҝҷжҳҜи·ҜйҒҘзҡ„ж•…д№ЎгҖӮ
жҲ–и®ёжҜҸдҪҚдҪң家зҡ„дё»и§Ӯдё–з•ҢйҮҢпјҢйғҪдҪҷжё©е°ҡеӯҳең°е‘өжҠӨзқҖзұ»дјјдәҺи·ҜйҒҘзҡ„жҜӣд№Ңзҙ иҝҷж ·зҡ„дёҖдёӘең°еҗҚпјҢжһ„жҲҗе…¶зІҫзҘһдёҠзҡ„ж №жҚ®ең°пјҢжәҗжәҗдёҚж–ӯең°иөӢдәҲе…¶зҒөж„ҹдёҺеҪ»жӮҹпјҢеҗҢж—¶ж°ёиҝңж— еҒҝең°з»ҷйӮЈдәӣж•Ҹж„ҹжҳ“зўҺзҡ„еҝғзҒөжҸҗдҫӣж— еҫ®дёҚиҮізҡ„ж…°и—үгҖӮиҖҢе…·дҪ“дҪң家зҡ„жҖ§ж јгҖҒж–ҮйЈҺд№ғиҮіз»ҸеҺҶпјҢйғҪдёҺе…¶зҒөйӯӮ家еӣӯзҡ„йЈҺж°ҙжҷҜиҮҙеӯҳеңЁзқҖжҲ–жҳҺжҳҫжҲ–жҪңеңЁзҡ„иҒ”зі»гҖӮ
дҪң家зҡ„еҠіеҠЁжҳҜе®қиҙөиҖҢиү°йҡҫзҡ„пјҢжҖ»жҳҜжңүжҹҗдәӣеә•и•ҙж·ұеҺҡзҡ„еӣ зҙ й»ҳй»ҳдёәеҠіеҠЁзқҖзҡ„дҪң家жҸҗдҫӣдәҶз»Ҳз”ҹжҸҙеҠ©——иӯ¬еҰӮдҝЎд»°гҖҒи®°еҝҶпјҢиӯ¬еҰӮ“ж•…д№Ў”иҝҷдёӘжҰӮеҝөпјҢж— и®әе®ғдҪ“зҺ°дёәзҒҜеЎ”еӯӨз«Ӣзҡ„иҫ№еҹҺгҖҒзІ—зіҷзӮҷжүӢзҡ„иҚ’жј жҠ‘жҲ–еӨӘе№іжҙӢдёӯзҡ„еЎ”еёҢжҸҗеІӣпјҲиҝҷдёӘең°еқҖеҸӘиғҪдҪҝдәәиҒ”жғіеҲ°й«ҳжӣҙзҡ„еҚ°иұЎжҙҫз»ҳз”»пјүпјҢеҚҙж°ёиҝңдҪңдёәжё©жҹ”д№Ӣд№ЎйҷҲеҲ—дәҺиүәжңҜ家жғ…ж„ҹзҡ„иҫ№зјҳгҖӮж•…д№Ўзҡ„жҰӮеҝөжң¬иә«е°ұжҳҜеҚҡеӨ§зҡ„пјҢжӣҙдҪ•еҶөжҳҜеӯ•иӮІдәҶеҚҡеӨ§зҡ„еҝғзҒөзҡ„ж•…д№Ўе‘ўпјҒ
еҗҲдёҠгҖҠж—©жҷЁд»ҺдёӯеҚҲејҖе§ӢгҖӢпјҢжҲ‘д»Қ然зғӯиЎҖжІёи…ҫгҖӮжӯЈеҘҪеҸӮеҠ жҙ»еҠЁпјҢжңүдҪң家жҠҠи·ҜйҒҘзҡ„жҲҗеҠҹеӣ зҙ еҪ’зәідёәиүәжңҜеӨ©иөӢпјҢиӢҰйҡҫз«Ҙе№ҙпјҢиӢұйӣ„жғ…з»“пјҢж”ҝ治家жҖқз»ҙпјҢиҙөж—Ҹж°”иҙЁпјҲеҗҺеӨ©дҝ®жҲҗпјүпјҢж®үйҒ“зІҫзҘһпјҢ并让жҲ‘жӢҝиҺ«иЁҖдёҺи·ҜйҒҘиҝӣиЎҢжҜ”иҫғпјҢжҲ‘еӣһзӯ”пјҡи·ҜйҒҘжҳҜиғҪеҒҡж»Ўжұүе…Ёеёӯзҡ„жң¬еңҹеӨ§еҺЁпјҢиҺ«иЁҖжҳҜдёӯиҘҝйӨҗд№ұзӮ–гҖӮеҪ“然пјҢд№ұзӮ–жң¬е°ұжҳҜеҗҚиҸңгҖӮиҺ«иЁҖжңҖеӨ§зҡ„жң¬дәӢпјҢдёҚд»…жҠҠдёӯиҘҝд№ұзӮ–еҒҡжҲҗдәҶдёӯиҘҝеҗҲз’§пјҢз«ҜдёҠеӨ§йӣ…д№Ӣе ӮпјҢиҝҳеңЁдәҺд»–еҠ иҝӣдәҶиҮӘе·ұдәәз”ҹз»ҸеҺҶзҡ„еҺҹжқҗж–ҷпјҢеҠ иҝӣдәҶиҮӘе·ұзҡ„й…ёз”ңиӢҰиҫЈпјҢи¶ід»ҘеҢ–и…җжңҪдёәзҘһеҘҮгҖӮиҝҷз§ҚйӣҶеӨ§жҲҗеҸҲдёҚеӨұиҮӘжҲ‘зҡ„еҲӣж–°ж„ҸиҜҶпјҢжҳҜи·ҜйҒҘжңӣе°ҳиҺ«еҸҠзҡ„гҖӮдҪҶи·ҜйҒҘжҳҜеҚ еұұдёәзҺӢзҡ„зәҜз§ҚдёӯеӣҪиҷҺпјҢеҖҹең°еҪўең°иІҢиҖҢеЁҒйЈҺеҮӣеҮӣгҖӮиҺ«иЁҖзҡ„е°ҸиҜҙеҲҷжҳҜж··иЎҖе„ҝпјҢд»–иҝҷжқЎжқӮйЈҹдё”жқӮдәӨзҡ„йҫҷеҸҜд»Ҙи…ҫдә‘й©ҫйӣҫпјҢеҸҳе№»ж— з©·пјҢи®©зңјиҠұзјӯд№ұзҡ„еӣҪдәәдёҺиҖҒеӨ–йғҪж„ҹеҲ°й«ҳж·ұиҺ«жөӢпјҢеӣ иҖҢдёҠеӨ©е…Ҙең°жқҘеҺ»иҮӘз”ұгҖӮеә”иҜҘиҜҙпјҢи·ҜйҒҘдёҺиҺ«иЁҖпјҢеҗ„жңүеҚғз§ӢпјҢжҳҜдёӯеӣҪеҪ“д»Јж–ҮеӯҰзҡ„дёӨеӨ§д»ЈиЎЁдәәзү©гҖӮ
гҖҠдёӯеӣҪ科еӯҰжҠҘгҖӢ (2018-03-02 第6зүҲ иҜ»д№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