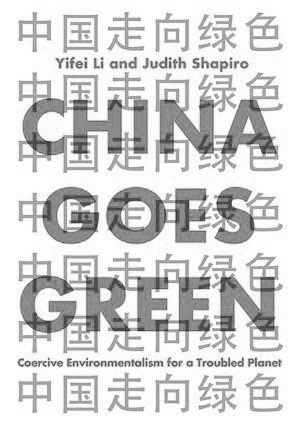
China Goes Gree: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Yifei Li、Judith Shapiro著,Polity Press2020年7月出版
我甚至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不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之成为“房间中的大象”。
传统西方观念总是把技术统治论等同于“机器乌托邦”,即它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大机器,而把每个人变成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无论是从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运动,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技术治理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刘永谋
China Goes Gree: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本文作者译为“中国走向绿色:适于危机星球的强制环境主义”,以下简称《中国走向绿色》)一书近来有些“火”,应该与作者之一的夏竹丽(Judith Shapiro)赫赫有名有关。
夏竹丽女士长期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长期深入中国中西部地区实地调研,在中国还收获了爱情。后来,她的博士论文从环境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设史,独辟蹊径,反响强烈,在中国也收获不少粉丝,尤其是在中国研究和环境史领域。
《中国走向绿色》延续了夏竹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一贯立场,对近年来中国在环境政策方面的转变,尤其是对生态文明的强调,进行政治哲学的深入分析,提出不少有趣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该书意识形态色彩太明显,论证先入为主的色彩太明显。
我认为,谈环境问题必须多一点技术,少一些意识形态。
正如本书所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实际上,环境保护意识当时在中国刚刚滥觞,有些欠缺实属正常。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与管理专业,那时环保产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因此毕业之后工作不好找。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提倡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尤其十八大以来,政府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整治环境,收效明显。
比如通过几年时间,北京雾霾频发的状况已得到极大的转变,即使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震惊,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以前保护环境欠缺,一些外国人批评中国为经济牺牲环境,中国人的健康权受到威胁;现在保护环境得力,一些外国人又批评中国用威权(authoritarian)方式治理环境,中国人的自由权受到威胁。保护环境不行,不保护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没有办法照搬美国,因为美式民主制很难为保护环境而采取集中措施,而这又是保护环境时必需的方法。
美国上一届特朗普政府退出相关环保条约,反映出很多美国老百姓不支持奥巴马政府的环保政策,觉得这些政策牺牲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对于环境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很多人讨论过,这里无需赘述。
环境保护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显然,一些学者在反思环境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存在问题,他们不知变通地固守一套陈旧观念不能说明现实,更不能应对问题。
民主制真的不能很好地应对环境问题吗?有些人认为,民主制不能采取集中式、强制性的措施。可是,谁说民主制只能等于无休止无结果的争吵呢?我不这么认为。
今日之美式民主制,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长期的反智传统和失去共识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此种民主制的确不适于应对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各方面利益,从技术上说需要集中统筹处理。
但是,民主制只能是今日美式民主制一种吗?更强调纪律的德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与美式民主制完全一样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与美国也根本不同。从理论上说,民主制不一定要“捆绑”极端个人主义、反智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认为,民主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一些高效的社会工程手段。当然,民主制也要控制此类技术治理措施,防止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制的基石。我们不能排斥所有的效率工具,简单地斥之为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是应该深入细致研究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调整和控制,使之为民主制服务。
在环境问题上,亦是如此。如《中国走向绿色》一样,简单地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归结为“威权环境主义”,然后或者为之辩护,得出环境问题正逼迫世界走向威权主义,或者专事批判,得出中国以保护环境为名大搞威权主义——此类意识形态争吵陷入二元对立思维,不能深刻地反映中国环境问题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争论中,地球环境在持续恶化。
在过去几年中,我集中研究技术治理理论。所谓的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中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的治理活动。在英语中,类似的讨论相当一部分是被归结为“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之下。但是,“技术统治论”一词带有相当的贬义色彩,故而我采用“技术治理”这一新概念,将技术统治论作为其中的一种,希望以更为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审视技术治理现象。
显然,进入21世纪之后,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全球性的基本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大大地推进了技术治理趋势。
2020年,我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德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德曼在《中国科学报》上讨论各国疫情技术治理模式比较,引发技术哲学界的强烈反响,富勒、尚伯格等学者纷纷回应。
不管观点和立场如何,没有人能否认技术治理在疫情应对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甚至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不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之成为“房间中的大象”(指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却一直被忽略的问题)。
传统西方观念总是把技术统治论等同于我所谓的“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即它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大机器,而把每个人变成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无论是从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运动,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技术治理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比如,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一经兴起就传入中国,民国时期尝试过,结果与美国差别非常大;而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尝试过“赛博协同工程”,具有明显的拉美色彩。
因此,技术治理不等于机器乌托邦,并不必然等于极权主义。民主制可以利用技术治理为自己服务,将之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名为《技术治理》的专著,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尝试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当代技术治理活动。
就环境保护而言,想要收到治理实效,任何国家都需要采取一些高效的社会工程措施,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威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指责不利于深入研究问题,尤其会阻碍民主制利用技术治理处理环境问题的努力。
当然,如此说并不是认为社会工程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比如效率不如预期、权力越界、某些人群生活受到影响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效率工具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更有建设性的态度应该是具体地分析其中的问题,更好地利用和控制技术治理。
总之,应对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但是太多意识形态、太少技术讨论,无益于治理环境和改善生态。
环境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从根本上都是价值观争论,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错。不要忘记,类似意识形态争论的目的,是为保护环境做更好的理论辩护。
因此,比意识形态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决心采取措施治理环境,并且为此做出牺牲——哪怕是牺牲一些便利,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原因就是人类希望在地球上延续得更长久一些。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疫情应对与技术治理》中,我提出“环境问题的科技谦逊主义”的观点,认为:(1)客观看待科技的力量;(2)要从“征服自然”彻底转向“敬畏自然”;(3)反对自然观的一元论,主张自然观的多元论;(4)从保护环境转向保证人类种族延续。
科技谦逊主义体现在传染病防控与应对的问题上,就集中体现为“敬畏病毒”的根本态度。
事实上,我并不赞同“环境保护”的说法,因为人类保护不了环境,环境也不需要人类的保护。
比如地球遍布塑料袋,被灭绝的肯定是人类,绝不是生命。地球经历过小行星撞击、大规模火山爆发,生命并没有被灭绝。许多显赫一时的地球物种消失了,例如曾称霸一时的恐龙。
反过来,生命又极其顽强,比如病毒,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在深海海底、在火山口,在完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都发现过生命的痕迹。所以,“保护环境”的说法有些狂妄。
人类之所以不要污染环境,是为了不要把自己毒杀。此次新冠疫情清楚地说明人类根本没有多强大,面对新冠病毒,人类保护自己都很吃力。
一言以蔽之,环境问题反思,可以多一点技术,少一点意识形态,如此更有利于人类真正行动起来。
《中国科学报》 (2021-06-24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