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揭榜挂帅 八年磨剑 |
|
中国科学家破解“柑橘艾滋病”世纪难题 |
|
|
4月的北京,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位于北五环奥运村附近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一栋科研楼的顶层温室内,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房顶和窗户,给碧绿的柑橘树、甘蔗苗镀上了一抹柔和的亮色。
研究员叶健轻抚着一株柑橘树油亮的叶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娓娓道来:这棵廉江红橙树是三年前的除夕夜从广东湛江运来的,当时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黄龙病,这是我国危害最严重的农作物病害之一。送来时,红橙树病得只剩枯枝。现在,你看,新叶和新枝都抽出来,花也都开了。”
 叶健在“巡视”温室里的柑橘树,这是他几乎每天要做的事情。冯丽妃摄
叶健在“巡视”温室里的柑橘树,这是他几乎每天要做的事情。冯丽妃摄
这株小树的旁边,同一批运来的另外两株对照柑橘树,根部腐烂,全株死亡。
“重焕生机”的柑橘树,正是中国科学家对柑橘黄龙病绝地反击的有力见证——一个困扰全球农业界长达百余年的难题,终于被撬开了突破口。
“几年前,我们携手国内柑橘病害研究最强团队,共同承担了‘揭榜挂帅’项目,目标很明确:精准阻击,遏制柑橘黄龙病在南方暴发的势头和向北扩散的风险。至于发文章、申请专利,都不在首要考虑范围内。”叶健对《中国科学报》说。
现在,经过8年抗战,他们不仅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顺带”申请了多个国内和国际专利,相关研究4月11日登上了《科学》,并被选为该刊封面论文。国际审稿人认为,该研究“令人信服,极具应用价值”。
 4月11日《科学》封面论文。
4月11日《科学》封面论文。
矿泉水瓶里的“风暴”
微生物所位于11楼的科研温室,或许是全北京位置最高的智能温室了——抗黑穗病甘蔗、抗黄萎病棉花、抗细菌病十字花科植物……这里孕育着许多抗病耐逆植物新品系。
叶健团队的温室内,靠窗一侧挂着几个简易的“点滴”装置:几个矿泉水瓶用室内高架上垂下的细绳笔直地倒挂在半空,一根根透明的输液管通过瓶盖上打出的小孔插入瓶口,不断将瓶内的液体通过“针头”输送到几株柑橘树的韧皮内。
 “打点滴”的柑橘树。冯丽妃摄
“打点滴”的柑橘树。冯丽妃摄
谁能想到,装在如此不起眼的矿泉水瓶里的液体,即将给饱受黄龙病摧残的全球柑橘产业带来一场风暴呢?
黄龙病,又称为“柑橘艾滋病”,是柑橘产业的头号杀手。其病原菌主要通过木虱传播,一旦柑橘树感染,叶片便会逐渐黄化,果实畸形、甜度降低、味同嚼蜡,枝、杆、根也会逐渐被侵蚀,短短3至5年整株果树就会枯死。
柑橘属植物包括橘、橙、柚和柠檬等,每年全球50多个国家的柑橘产业因黄龙病造成的损失超过百亿美元。这种细菌性病害无药可治,农民对付它,只能依靠“三板斧”——采用无菌苗、杀虫、砍树。但这些都“治标不治本”,病原菌依旧会肆虐,带来死树毁园的致命打击。
在我国,黄龙病每年会给柑橘产业带来超过100亿元的损失。2013年到2016年,为了遏制肆虐的黄龙病,赣南三年间砍掉了近4100多万棵脐橙树。
 绿色嫩芽上的棕色木虱。
绿色嫩芽上的棕色木虱。
 柑橘木虱。
柑橘木虱。

开始发病的柑橘树,果实尚能正常生长,三年后就会大幅减产。
 广西南宁为防木虱给柑橘树喷洒石灰水。
广西南宁为防木虱给柑橘树喷洒石灰水。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红山万亩柑橘产业园,该园始建于2001年,2014年开始零星感染黄龙病,2020年集中爆发,现已灭园。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因染病被砍伐的柑橘园。
2017年,叶健第一次到赣南做黄龙病采样,看到的景象让他痛心不已:有的农民不愿意砍树,抱着树杆哭,有些老人甚至用生命护树。“砍树对他们来说损失太大了,一棵健康的果树能收200斤左右果子,收入1000多元,而且脐橙树要8年才能达到盛果期,尽管国家给老百姓补贴了很多钱,但没了树他们就没了经济来源。”他说。
这让叶健下定决心,啃下黄龙病这块“硬骨头”。
2018年至2024年,农业农村部先后设立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以及柑橘黄龙病“揭榜挂帅”项目,号召科学家联合攻关柑橘黄龙病。在这个领域刚刚起步的叶健,带领团队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七年时间里,与合作者攻下从理论到应用的一个个难关,打开了改写柑橘产业命运的那扇门。
温室内,副研究员赵平芝指着简易的“点滴瓶”,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这些液体中就含有我们用AI设计的小肽药物,1毫克可抵5克抗生素,能精准破坏柑橘黄龙病病原菌的膜结构,而且不用担心耐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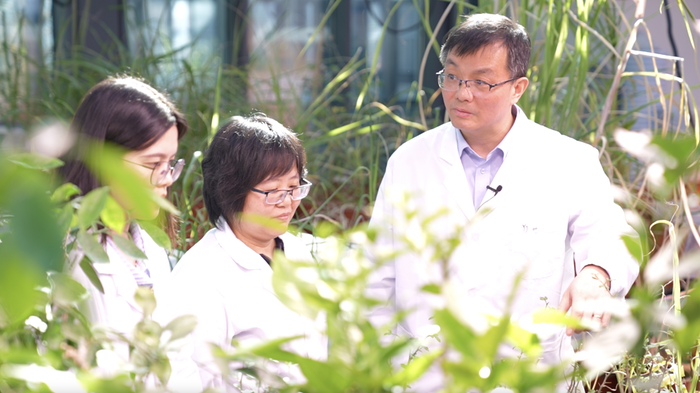 叶健、赵平芝、博士生杨欢在温室查看柑橘树。丁典摄
叶健、赵平芝、博士生杨欢在温室查看柑橘树。丁典摄
揪出关键基因,“自带疫苗”育种呼之欲出
“你们上次在这里做试验,现在荒树大部分都冒出新芽了,而且新芽能转绿。这说明你们的方法很有效,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检测一下?”叶健的微信里,有这样一条来自广西自治区南宁武鸣区上林县巷贤镇新生村村民刘建领发的视频。
2023年和2024年秋天,叶健与赵平芝带着学生把温室里的实验搬到了广西与赣南的柑橘荒园里,他们就像一群“树医”,给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病树“打点滴”。几个月后,打了小肽的树发出茂盛健康的新芽。
田间数据也令人振奋:注射6个月后,病原菌基本清零,果实糖度从低于10提升至16,接近17.5度的“钻石级鲜橙”。而荒园里“未打点滴”病树或只剩焦叶残枝,或早已枯死。
如此显著的成效,让当地的村民们自告奋勇地帮他们做“免费观察员”,随时反馈果树的变化情况。“看着农民说枯树发芽,其实我们比发顶刊论文还高兴。”叶健看着手机里果农发来的视频笑言。

健康和感病(带绿色)的柑橘果实。
 感染黄龙病的“红鼻子果”。
感染黄龙病的“红鼻子果”。
长久以来,因为药物防治手段对黄龙病无可奈何,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发达国家也不得不对此采取“极端手段”。如美国在2021年批准使用剧毒杀虫剂涕灭威防控木虱。但早在2003年,涕灭威就因为对人类造成健康问题被欧盟禁用。中国市场自2020年10月起也禁含涕灭威产品在境内销售和使用。为了防控黄龙病,提振柑橘产业,美国还批准在橘树中使用链霉素(抗生素)来防控毁灭柑橘树的病菌。
“过去,我国也有农民会用四环素治疗黄龙病,这虽然能暂时挽救病树,但最多只能维持一两年,而且会产生面源污染和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叶健说,“我们的小肽不仅效果比四环素好,而且是从人类肠道菌中筛选出来的,在生态和食品上都更具有安全可持续性。”
叶健解释说,黄龙病菌是一种胞内菌,会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柑橘细胞内,难以清除。而小肽就像一个医用“电钻”,会在病原菌的细胞膜上穿孔,从而导致细菌的细胞内容物外溢而死亡。据悉,这项技术已申报我国发明专利6项,国际专利3项。
如此“对症”的“药方”并非凭空而来,研究团队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为它提供了基石。
一直以来,攻克黄龙病的难点在于一直找不到抗病基因。这就像射击时没有靶子,又如何能命中目标呢?
为了破解难题,叶健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时间尺度——2000多万年来芸香科植物的进化史。“花椒、咖喱、九里香等都是柑橘的芸香科‘远亲’,它们有的对黄龙病天生免疫,有的虽然病菌能够繁殖,但毫无症状。叶老师认为它们的基因里或许藏着抗病的‘钥匙’。”高级工程师孙艳伟解释说。
研究团队分析了十余种芸香科植物的基因组信息,首次发现其中都存在黄龙病抗病基因——植物茉莉素信号通路核心转录因子MYC2。然而,与其互作的另一个基因——E3蛋白降解泛素连接酶PUB21却会降解MYC2,导致柑橘失去对黄龙病的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芸香科抗病植物中存在多了一个基因拷贝的突变基因——PUB21DN,它能阻止PUB21发挥蛋白降解功能,从而稳定MYC2抗病蛋白,使柑橘获得对黄龙病的高抗甚至免疫能力。
“PUB21和PUB21 DN就像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前者是植物抗病免疫网路的‘叛徒’,会抑制抗病基因;后者是‘守护者’,能管住PUB21,让MYC2正常执行杀菌功能。”叶健解释说。
揪出抗黄龙病的关键基因靶标后,研究团队不仅挖掘出了治病的小肽,还打开了抗病基因育种的新通道。当把PUB21 DN导入感病植物后,就能赋予柑橘树抗性,甚至是创制出“自带疫苗”的新品种。
“叶健和团队利用人工智能找到适合的小肽,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实现了黄龙病的可防可治,是一个重大突破。他们还找到了关键的抗病基因,对于作物育种来说,这个抗病基因就相当于‘农业的芯片’,对于重塑全球数千亿美元的柑橘产业格局意义重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方荣祥说,这项成果发表后,全球势必会开发和转化小肽生物农药产品,同时推进相关基因编辑育种。
“我们要做好专利保护,推动相关成果落地,动作要快!”他说。
 方荣祥(右二)与叶健、赵平芝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刘黎琼摄
方荣祥(右二)与叶健、赵平芝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刘黎琼摄
三代人接力,创建“中国人自己的赛道”
叶健告诉《中国科学报》,这项科学突破是师生三代人接力传承的成果。
“这个成果最重要的还是受到方老师思想的影响,他经常教导我们,要挑最难、最重要的课题来做。”叶健对《中国科学报》说,“我记得回国那年,方老师说‘科研就像种树,要耐得住十年寂寞’,才能在传统农业领域建立自己的赛道,实现‘换道超车’。”
2014年,叶健响应方荣祥的召唤,放弃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员职位,在微生物所副研究员的岗位上投身虫媒病研究。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舍弃“不算什么”,方荣祥院士当初面向国家粮食安全重大需求,为解决我国病毒引起的马铃薯品种退化问题,毅然跨界,从人类流感病毒研究转向植物病毒研究。他希望能追随老师的脚步,在国内的科研舞台上一展抱负。
叶健很感恩自己背后有一支能吃苦、不怕碰壁、敢于挑战的团队。
在“揭榜挂帅”项目汇集的“各路人马”联合攻关团队中,叶健带领的这支年轻的团队显得有些稚嫩,但他们内心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不解决问题,就不发文章。这篇论文也是该课题组过去八年在这个领域发的唯一一篇研究成果。
田间试验碰到了不少“钉子”。最初,他们想让农民帮助做试验,但农民总认为叶子变黄是缺肥导致的,再加上害怕砍树会带来损失,所以很难配合。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废弃的荒园做试验,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病树需要被地方强制砍掉,他们在广西和赣南的柑橘荒园里给果树“打点滴”、用石灰防木虱、给果树罩防护网,可次年刚见成效,树就被砍掉,只能从头重来。
赵平芝和孙艳伟是团队成立之初就跟着叶健“打江山”的“老人”了。两人都是实验室里的“拼命三娘”。赵平芝为了开展田间试验,变身“空中飞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广西、江西多地。她晕车严重,在广西、江西的山路上更是吃了晕车药也无济于事,但吐完了,忍着头疼与不适依旧上阵。孙艳伟为了找到合适的实验材料,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团队里的“包打听”,向西南大学教授周常勇等多方搜寻芸香科植物资源。她还带着学生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摸索,为实验室建立了九里香、咖喱、道县野橘等植物以及柑橘木虱的养殖方法,建立了植物组培和基因编辑研究平台,确保用稳定的实验材料产生高质量的数据,最终找到了核心抗病基因MYC2。
 叶健(右二)和论文三位一作孙艳伟、赵平芝、杨欢(从左至右)。冯丽妃摄
叶健(右二)和论文三位一作孙艳伟、赵平芝、杨欢(从左至右)。冯丽妃摄
团队里的年轻学生们也是“生力军”。博士生杨欢记忆最深刻的是,为了检测小肽田间试验效应,她和师弟师妹一次能采集几大袋子柑橘叶片,装好几百个离心管来提取DNA,工作量极大。但正因为如此,研究团队才有了两年的大量田间高质量的小肽防效数据积累。
让杨欢更有成就感的是,她们还“白手起家”,学会了用柑橘外植体创建柑橘基因编辑小苗,为下一步的新种质创新打好了基础。“每当科研中遇到问题和困难,老师们就会引导我们自己想各种办法去解决,这锻炼了我们的独立探索精神。”她说。
“作为导师,我们是一个梯子,要做好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一个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我们踢出了破门第一球,更多的胜利还是要靠更多的人才,一代接一代去努力拼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柑橘产业核心‘卡脖子’难题。”叶健说。
下一步,等待他们探索的还有很多,比如柑橘亚科植物为何随着2000万年前青藏高原逐渐隆升和喜马拉雅山的出现,丢掉PUB21DN这个抗病基因,从而培育因地制宜、以种适地的抗病柑橘新品种。
“不过,至少现在,战胜黄龙病,我们有了主动权。”叶健说。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dq7203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