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Nature前高管加盟复旦创办研究院,不设“非升即走”考核 |
|
|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李思辉 实习生侯婧怡
在国际科技期刊出版领域,杨晓虹是近年来最活跃的华人面孔之一。
从《癌细胞》《细胞》,到《自然》,再到《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又回到《自然》,过去十多年间,她在多家顶刊及其出版集团担任执行主编、副总裁等职务,亲历了中国科学家从顶刊“零星发表,少为人知”到“全面井喷,惊艳全球”的跃升,并且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杨晓虹选择放弃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副总裁职务,全职加入新成立的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院,出任该院首任执行院长。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上海独家专访了杨晓虹。她谈到了对中国科技成果“走出去”情况的观察、对学术发表问题的见解,以及关于自身跨界发展的思考。
 杨晓虹近照复旦大学学敏高研院供图
杨晓虹近照复旦大学学敏高研院供图
20年来中国CNS发文呈井喷之势
《中国科学报》:有科学家说,你在CNS(《细胞》《自然》《科学》)的工作经历很传奇,那是一段怎样的职业历程?
杨晓虹:
我可能是CNS系列的第1.5代华人编辑。事实上,我开始担任全职科学编辑的2008年乃至更早的时候,发表在CNS上的中国研究成果非常少,来自中国的编辑则更少。
2008年底,我还在哈佛医学院暨麻省总医院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肿瘤。
适逢细胞出版社旗下的《癌细胞》面向全球招聘一名学术编辑,我对编辑出版又比较感兴趣,于是就试着应聘这份工作。
当时,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的非英语母语背景是否会成为障碍。得到的答复是开放且专业的:“没关系,我们看重的是你的科学素养。”
全职加入《癌细胞》之后的10年,我扎根在细胞出版社的波士顿总部,从科学编辑、高级编辑成长为常务主编,并且在2011年至2018年间兼任了细胞出版社中国及亚太地区发展事务负责人,在2014年至2017年间兼任《分子植物》的全球出版人。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全面地了解了国际高质量、高影响力专业期刊的运作。之后,我还作为代常务主编在《细胞》主刊工作了一年多。
2018年秋天,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主动邀请我回国,担任集团大中华区的科学总监兼《自然》系列期刊执行主编。离国多年,能够回到国内工作,无疑很具有吸引力。于是我没有任何犹豫地从波士顿搬到了上海。
另外我也出任过《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的共同出版人和共同主编,深度参与了其旗舰项目“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在亚洲与中国区的评选。这让我得以接触到一大批极具原创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中既有非常专注基础研究的,也有积极创业投身产业化实践的,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科技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担任总监、副总裁等职务期间,我的日常工作也从稿件处理逐渐转向了更宏观的层面。比如,编辑团队建设、期刊发展战略、开放科学、科研诚信体系与评价体系的建立等。
作为集团包括《自然》系列期刊的一名代表,我一方面非常珍视并保持与国际科学界、出版界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拓展了与中国科研院所和科学家团体的联系。参加学术讨论,访问高校,走进科学家的实验室……这些始终是我工作中最富活力的部分。
《中国科学报》:据你观察,过去近20年里,中国科学界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杨晓虹:
从高水平的文章上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飞跃”——一场在数量与质量上同时发生的惊人跃迁。
在我2008年底加入细胞出版社时,来自中国科研团队的稿件数量非常有限,能够通过编辑部内审进入外审环节的寥寥无几,最终能发表的更是凤毛麟角。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与中国科学报社的一项里程碑式合作——“中国科学家与Cell Press”。从2014年开始,细胞出版社和中国科学报社一道,每年统计并出版一期特刊,系统梳理中国科学家以中国机构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细胞出版社旗下所有期刊上发表的工作。2014年,这个数字只是一百篇出头,2015年甚至还下降了一点。当时我们可以用一整版的篇幅来详细介绍每一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和作者访谈。
中国研究人员在细胞出版社旗下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在这之后一路攀升,从两百篇、五百篇,到突破千篇,如今甚至达到了数千篇的规模。以至于现在我们如果出版一本年鉴类的特刊,可能每篇文章只能以寥寥几行作为介绍了。
更重要的还是质的飞跃。早期的投稿,或许更多的是“达到”顶刊的发表标准。但如今,来自中国的许多重要科研工作,已经不仅仅是“达标”而已——它们完全能够代表所在领域的全球性的重大突破,有些甚至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和影响力。
从几乎空白,到在全球顶尖的科学期刊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只用了不到20年。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亲历者,我为之兴奋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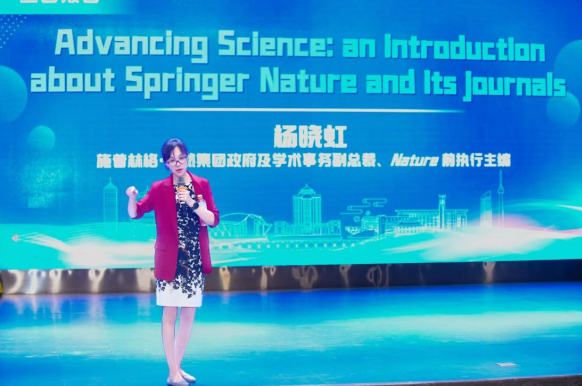 杨晓虹在第十六届创新发展论坛上李思辉/摄
杨晓虹在第十六届创新发展论坛上李思辉/摄
不能简单粗暴地以CNS衡量科研价值
《中国科学报》:当前国内对于“唯CNS论”的讨论很多,你对此怎么看?你认为眼下国内的科研评价有何待改进之处?
杨晓虹:
我的观点很明确:不应该“唯论文”,更不应该“唯顶刊”。
发表科研论文的本质是什么?论文是知识传播的一种载体和形式,它是一份经过了同行评议的正式的学术记录,以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让科研不断延伸迭代。包括CNS在内的学术期刊虽是实现这些功能的重要平台之一,但并非唯一平台。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项科研成果能否在某个特定期刊上发表,存在一定的偶然性。CNS这类综合性顶刊容量非常有限,它们也有自己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偏好等。比如数学研究,数学界的四大顶刊(《数学年刊》《数学新进展》《美国数学会杂志》和《数学学报》)可能远比CNS更受数学界青睐。
再比如,历史上有些非常重要的成果其实是发表在一些比较“小”甚至不知名的期刊上,并非发表在CNS上,但这并不影响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也有人调侃,“如果爱因斯坦活在当下,估计发不了顶刊”,这实际上也是可能的。顶刊当然希望不遗漏任何好的成果,但科研成果浩如烟海,谁都无法保证不会出现沧海遗珠之憾。因此,我们有一个共识:被拒稿完全不能代表某项工作不好。
此外,预印本的兴起也正在深刻改变“游戏规则”。特别是在物理、计算科学等领域,一些学者更早地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接受整个学术社区“众筹式”的评议。这种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它本身就是对传统期刊评价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所以,不论是在公开演说的场合,还是与年轻科学家面对面的时候,我都始终鼓励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人,不要因为一两次被顶刊拒绝而气馁。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其光芒不会因为它发表在何处而被永久埋没,时间自会证明一切。
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更加多元化、更符合不同学科特点的评价体系,而不是一把简单的甚至是粗暴的“CNS尺子”。
全职加盟国内高校为的是“做一件大事”
《中国科学报》:从学术编辑到顶刊集团副总裁,你已在国际科技出版界颇有建树,为何选择此时到国内高校任职?
杨晓虹:
这确实是我职业生涯中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契机始于今年春天,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联系到我,谈及他们计划依托120周年校庆的捐赠,创办一个新型的高等研究院——学敏高等研究院。其愿景非常清晰:面向全球,不限学科,支持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性”研究。
这个理念深深地触动了我。它让我想起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卡文迪许实验室甚至我成长的冷泉港实验室等科学史上的传奇之地。它们无一不是通过营造纯粹、宽松、自由且独立的学术环境,孕育出了一大批划时代的成果。想到能够更贴近科学家和科研一线,亲身参与打造一个支持下一代科学领袖的“摇篮”,我感到非常振奋。
所以,我最终决定辞别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全职加入复旦,出任学敏高研院的首任执行院长,并在学校的支持下,负责这个新型“学术摇篮”的创建工作。这对我而言,既是一次回归,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要做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大事”。《中国科学报》:这个高等研究院的定位与发展愿景是什么?
杨晓虹:
在筹建过程中,我们深入研究了国际上不少成功的模式,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思路。对于学敏高等研究院的“独特性”,我们初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定的年轻化。我们将目光坚定地投向90后、95后这批最具原创活力也最贴近新技术发展趋势的科学家、工程师等学者群体。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思维不受传统范式束缚。我们深信他们中必然蕴藏着未来的诺奖得主。
二是颠覆性的支持模式。我们致力于提供长期、稳定、充足的经费支持。在这期间,我们不设置短期的、硬性的考核指标,没有“非升即走”的压力,旨在彻底解放科学家,让他们敢于去挑战那些“十年磨一剑”的重大基础难题。
三是跨学科的基因。我们坚信,未来的重大突破必然源于学科的交叉碰撞。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自我设限,而是围绕重要科学问题,而非传统的学科目录来组建团队。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从微物质、微生物到大脑、大宇宙,以及其他富于创造性的学科交叉都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四是全球化的视野与本地化的生态。我们不仅要吸引中国最优秀的大脑,更要面向全球招募英才。为此,我们特别设计了“访问学者项目”,便于国际顶尖的学者以短期来访的形式,在上海、在复旦生活和工作一个学期或一个夏天,亲身体验这里的科研生态和生活环境。
我们希望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院能成为一张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科学名片,一个让年轻天才们能够自由探索、勇敢冒险的学术乐园。这条路需要更多科学家和我们一起谋划、共同开创。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