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唯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我与珍·古道尔的27年师友情 |
|
|
文 | 郭耕(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10月2日一早,惊悉世界著名灵长类学家、联合国和平使者珍·古道尔在美国加州巡讲途中溘然长逝,享年91岁。她的辞世既出人意外又平静自然,我乍一听说,不敢相信,与几位朋友核实后,才敢上网发文祭奠。
对任何人来说,在这个年龄还能游走于世界各地,都算达到了人生“活得久,走得快”的完美境界,但是作为一个贡献卓著的动物学家和环保人士,珍博士的离开对世界、对人类、对大自然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我与珍博士早在1998年就相识了,是同行,更是师友。我们都曾接触黑猩猩,所以见面后有很多相关的“行话”可讲。她是我最尊重的老师和前辈,也是最仗义的有求必应的朋友。
 珍·古道尔(左)与郭耕。
珍·古道尔(左)与郭耕。
?
珍博士非常爱中国。她多次来华,无私奉献智慧和培养环保新人的义举证明了这点。1998年到2024年,珍博士17次来到中国,而我有幸在她第一次来中国时便与她结识,并带她参观了北京麋鹿苑,为她讲述了一只叫“大壮”的白唇鹿的故事。而她则推出了一个科普创意: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是谁?
那是1998年11月15日下午,正巧有位小学校长带着孩子们到麋鹿苑。孩子们的到来,把气氛推向高潮,大家纷纷围着珍博士要签名。珍博士不厌其烦地签下“Jane Goodall”,一个男孩儿问珍博士:“你为什么给我写了个600呀?”那其实是Goodall的英文。当我翻译给珍博士后,她对那个男孩儿流露出了既无奈又爱怜的表情。
当晚,珍博士在原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进行演讲活动。我又追到那里,将她下午推荐的科普创意小样做出来交给她。这一举动得到了珍博士的赞赏,给她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后来,她再来中国做演讲,总能从座无虚席的观众群里看到我并喊我上台。
之后珍博士连续10年来中国,她的演讲我场场不落。一次,她深入基层给小学生做演讲,恰好去了我女儿的学校。女儿回到家,兴奋不已地向我们讲述珍博士的故事。
我撰写的一篇关于珍博士与黑猩猩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后来,我还翻译了珍博士写的走访北京麋鹿苑和研究乌邦寺庄园麋鹿的文章。
每次珍博士回国后总会给我寄来明信片或个人著作,并附上共勉之语。我也在每次她来时赠予我写的书,特别是应她之需,赠送了一只麋鹿角,以便她巡回各处讲述麋鹿保护的成功案例。
珍博士是一位非常讲义气的人,有环保主义者的仗义。当我的新书《动物与人随笔》和《动物与人那些事》即将出版时,编辑听说我与珍博士很熟悉,都提出建议,请她写荐语。我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但通过工作人员向她提出请求后,她几乎有求必应,而且写了许多。也有国内出版社编辑听说我与珍博士是好友,约我为她出版的书写序言或荐语。我曾为珍博士《大地的窗口》书写序言,为《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写推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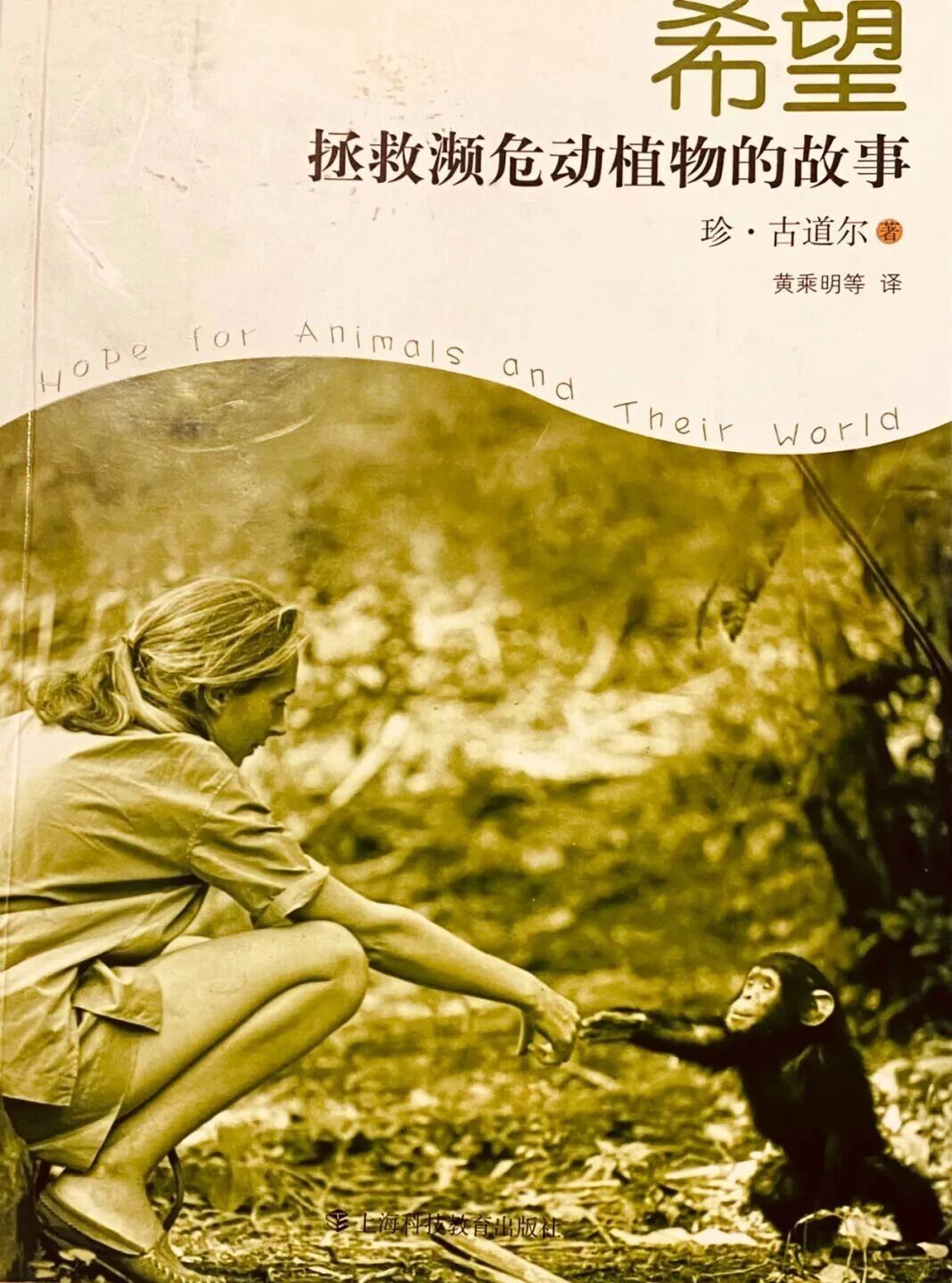 珍·古道尔在中国出版的图书《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封面。作者供图
珍·古道尔在中国出版的图书《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封面。作者供图
?
2008年12月6日,珍博士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做了主题为“自然的希望”的演讲,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梁从诫先生充当翻译,我做主持人,配合十分默契。
此后这些年,珍博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追随者越来越多,因为每次她来去匆匆太辛苦,怕占用她宝贵的时间,我只是默默关注她。
2024年11月,90岁的珍博士再度来华,我本要去看她,可惜此前有其他邀约,没能与她再见,成了终生憾事。
我印象最深且觉得翻译歧义最多的是珍博士那句三段式名言——“唯有理解,才能关心;唯有关心,才能帮助;唯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最后一句经常被大而化之地译成“唯有行动,才有希望”,我不认同,原因来自她说这句话的前因后果。
每当她来中国,我总会追随并聆听珍博士的演讲,我发现,她的思想在不断完善与升华。记得第一次听她讲这段话时,她说:“唯有理解,才能关心;唯有关心,才能帮助;唯有帮助,它们才能被拯救(They will be saved)。”后来,她将其改为“唯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Shall all be saved)”。这句话蕴含的智慧极其深刻:拯救他者,也是拯救自己;博爱他人,也是自爱之道。遗憾的是,这句话常被误译。
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共有3位女弟子,分别是研究黑猩猩的珍·古道尔、研究山地大猩猩的戴安·福西、研究黄猩猩的比鲁捷·嘉蒂卡斯。珍博士在公众面前是一名勇敢的黑猩猩研究者,但她绝不只关注黑猩猩,而是以博爱的情怀关注大自然、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野生生灵,包括被不少人厌恶的鬣狗。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