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被重新“发明”的传播学—— |
|
病毒、金融风暴、谣言、肥胖,是一回事吗?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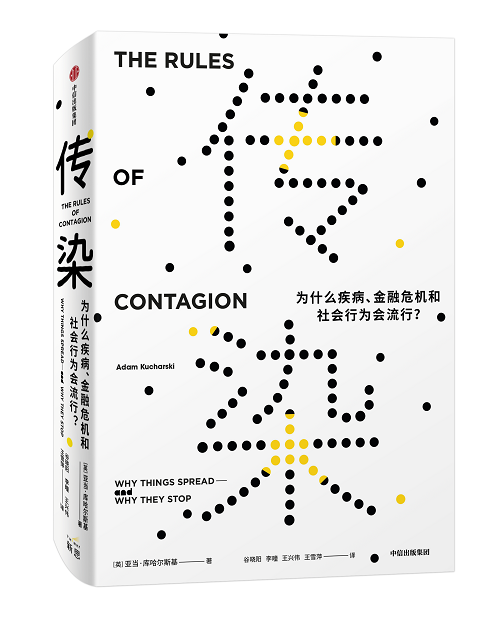
[英] 亚当·库哈尔斯基著,谷晓阳、李曈、王兴伟、王雪萍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出版,69元
2020年即将过去,可弥漫在整个世界的恐惧、不安、焦虑、悲伤统统没有过去,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望不到头的传染病。
传染不是病毒特有的。事实上,在人的社会行为中,传染无处不在。观念、行为、讯息及产品经常会像病毒一样发作蔓延,比如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效果显著的网络营销、广泛传播的网络谣言等等,它们的本质就像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瘟疫。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系副教授亚当·库哈尔斯基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的一线,他还新近出版了《传染》一书,梳理了流行病学传染模型的研究历程,并用传染病学的话语体系来回答公众,为什么疾病、金融危机和社会行为会流行。
S型曲线和创新扩散
了解流行病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展开,预测流行病爆发的过程以及各种干预措施可能会如何影响流行病,是当前各国政府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策略的基础。而这样一套流行病学传染模型的奠基者是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
罗斯并不是第一个用数学方法描述流行病的人,但他是最早用数学公示总结出了一个疟疾传播的概念模型,并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和预测疫情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人。他也因此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罗斯把传染的趋势表示为一跟拉长的S型曲线。刚开始的时候,受影响的人呈指数级增长,因为易感人群非常庞大。在到达一个高峰点后,增长就会逐渐慢下来,因为易感人群逐渐减少,康复人数会大于新增感染人数,直到增长停止。
S型曲线是流行病传播的典型趋势,可就在半个世纪后,传播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却将它用在了一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领域。
众所周知,创新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但这样的描述容易让人忽略一个环节,那就是“扩散”。创新只有得到广泛的扩散,才能产生真正的经济影响。
而罗杰斯在著作《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指明,20世纪,收音机、冰箱、电视、手机的流行都遵循这个S型曲线模型。
在扩散的早期,新理念、新产品的采用者很少,进展速度也很慢;当采用者人数扩大到居民的10%~25% 时,进展突然加快,曲线迅速上升并保持这一趋势,即所谓的“起飞期”;在接近饱和点时,进展又会减缓。整个过程类似于一条“S” 型曲线。
扩散早期的采用者,是愿意率先接受和使用创新事物并甘愿为之冒风险的那部分人,看似“势单力薄”,但这些人不仅对创新初期的种种不足有着较强的忍耐力,还能够对自身所处各群体的意见领袖展开”游说”,使之接受以至采用创新产品。之后,创新又通过意见领袖们迅速向外扩散。
罗杰斯认为,扩散总是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进行,在这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提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同时,人际交流能促进人们接受和使用创新。他也因此提出,创新推广的最佳途径是将信息技术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加以应用。
从此以后,S型曲线在社会学领域大受欢迎。可这远不是罗斯当初的终极目标。库哈尔斯基将他的理想描写为,借传染的数理模型来解决与统计学、人口学、公共卫生、演化理论,甚至商业、政治相关的问题。
R值和谣言遏制
1911年,罗斯曾写下一句话:流行病学实际上是一门数学学科。然而,直到R值的出现,流行病学才彻底走向了数学的“康庄大道”。
20世纪50年代,疟疾研究学者乔治·麦克唐纳在罗斯之后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如果一名感染者来到一个群体中会发生什么?会产生多少新发感染病例?
20年后,数学家克劳斯·迪茨提出了“再生数”(R值)概念,又称“传染数”,指的是一个感染者预期平均可能导致的新发感染的人数。
再生数的出现,成为了理解“传染的法则”的关键,因为它可以用来推测疫情是否会大爆发。
如果R值小于1,那么每一位感受者将平均产生不足1起新发感染,这样,新发病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相反,R值大于1,新发感染病例会不断增加,可能造成疫情大流行。
R值是可以被影响的,与之相关的有4个因素:患者具有传染性的时间长短,也就是传染期;患者传染期内每天传播感染的平均机会数;每次接触时发生传染的概率;人群的平均易感性。
通过这四个因素,不仅可以弄清传染机制,也是找到控制传染病方法的关键。
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不仅受到病毒威胁,也常常受困于信息的流行病。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虚假消息、谣言传播极快,波及甚广,信息流行病也亟需管控,而研究者又能从R值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库哈尔斯基介绍,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地震发生后3小时,一名推特用户声称,一个液化石油气储罐发生了爆炸,即将导致天降毒雨。储罐爆炸是真,毒雨却是子虚乌有。然后,一天之内,成千上万人浏览并分享了这个虚假警告。
针对这一传言,当地市政府在推特上发文辟谣,第二天晚时,转发辟谣消息的网友人数已经比原来转发谣言的网友人数多了。日本一个研究团队利用数学模型估测,辟谣消息如果再早两个小时,谣言的暴发范围还会减少25%。
另外,库哈尔斯基还提到,脸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用户迅速向分享虚假消息的朋友指出问题,后者删除内容的而概率可以高达20%。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媒体公司还会通过改变应用程序的结构,故意减慢传播的速度。比如在印度,谣言爆发后,WhatsApp为转发内容设置了障碍,印度用户只能把消息转发给5个人,而不是先前的超过100人。
这些反制措施其实就是针对R值的不同影响在起作用。日本政府的及时辟谣,降低了人群对有害信息的易感性;脸书用户的劝说,减少了有害信息的传播时间;WhatsApp的管理则减少了传播的机会。
“再生数还有最后一个影响因素:信息所固有的可传播性。”库哈尔斯基特别强调。在对网络“传染”的研究中发现,媒体在恶意信息传播中常常发挥着广播放大效应,否则一些极端思想是很难传开的。因此,如果一个观点变得流行,网络意见领袖、媒体常常有意无意地助长了传播。这也在提醒媒体需要反思应对恶意理念的方式,以限制潜在的“传染”效应。
超级传播者和金融危机
虽然R值是现代传染病暴发研究的核心,但有时R值也会失效。
关于疾病的暴发有过一个错误的看法,每个患者会传染相同数量的人。直到1997年,一些流行病学家提出了一个“二八法则”。他们发现,类似艾滋病和疟疾这样的传染病,20%的病例引发了约80%的传播。当年的SARS,也与之相似。
这20%的“核心人群”就是超级传播者。如果疫情中出现了超级传播事件,就意味着某些人在疾病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于是,流行病专家对此展开了研究:传播网络中的个体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感染风险?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能识别高风险人群,从而有助于在早期阻断暴发。
过去只是流行病专家关心超级传播事件,直到十多年前,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降临。
2008年9月15日,对闻名遐迩的华尔街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库哈尔斯基注意到,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开始思考金融系统危机的“传染”问题了。
一般来说,银行之间的连接不是均匀分布的,少数银行在网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引发超级传播事件的可能性就远大于其他银行。
危机爆发前两年,研究人员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合作,对美联储资金转账系统支付网络的结构进行了拆解分析。在对数千个银行间一天内发生的1.3万亿美元的资金往来进行仔细研究后,吃惊地发现,75%的资金往来都发生在66家机构之间。
库哈尔斯基解释,根据流行病学研究的结论,这些大型银行与网络中的其余成员的连接方式属于“异配性网络”,高危个体主要与松散存在的低危个体形成连接。在异配性网络中,感染在初期阶段的传播速度较慢,但最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流行。在雷曼兄弟倒闭时,它与超过了100万个机构存在贸易往来。
库哈尔斯基表示,正是经历了这场风暴,现在流行病学理论的启示正在被付诸实践。金融监管需要明确哪些银行处于网络的中心,要让那些居于重要位置的银行持有足够的资金,以降低其对“疫病”的易感性。
此外,也要对机构间的网络连接采取措施,但是想要调整金融网络的结构非常困难。而且,由于银行会保护商业活动信息导致数据缺乏,所以研究人员很难厘清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就很难对可能蔓延的危机进行评估。网络科学家们发现,在研究危机的发生概率时,有关借贷网络的信息只要有微小的偏差,评估得出的整个金融系统层面的风险就会出现巨大的误差。
在库哈尔斯基看来,这也是金融传染比病毒传染更为复杂的地方。
肥胖也可以传染?
到此,人们不难理解,病毒、金融危机、流行文化背后都有一只“传染之手”,这些事件被罗斯定义为依存事件,也就是说,某一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概率取决于目前有多少其他人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
与之相对的是事故、理论和慢性病等“非传染性”事件,罗斯认为,这些事件是独立发生的,并不存在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到了21世纪,科研人员也开始怀疑起了这一认识。2007年,一篇名为《32年来肥胖在大型社交网络中的传播》论文在发表后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长期跟踪分析了这些参与者的健康数据,提出了一个观点,肥胖可能在朋友之间传播,还可能在社交网络引发连锁反应,潜在地影响朋友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研究者还研究了社交网络中其他的社会“濡染”问题,包括吸烟、幸福、离婚、孤独。
这样的结论自然收到了很多批评,质疑者认为这一因果关系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事后推导。
事实上,人们经常与认识的人有共同的特点,从健康习惯、生活方式、政治观点到经济水平。可能的原因包括社会濡染,相互习得;同类相聚;相同环境的影响。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库哈尔斯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引发一次“疫情”,并进行观察。也就是引入某种行为,看它如何传播。并且将实验的结果与随机选择的对照组,也就是没有接触这种行为的人群进行比较,来判断引入这种行为的影响到底的有多大。这是一种理性又大胆的想法,但在实验设计的可行性和伦理问题上又难以获得支持。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看来,社会“濡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传染机制,而“数学模型更理想化,适合研究对每个个体的动力机制高度相似的‘传染’现象,比如用R值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病毒地传染。但如果‘传染’动力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大相径庭,统一的模型就难以建立。即使能够建立,也很难搞清楚其具体机制,无法判断该模式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自杀、暴力、童话、社交平台爆款文章就是这样一类事件。”
“从目前来看,流行病学的传染模型在解释复杂传播现象时,还是显得力不从心。”刘海龙说。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向而行”
库哈尔斯基一直致力于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破解疾病、思想、行为传播背后客观的驱动力,以及暴发模式背后的动因,以助于人们获得新的启示。
“这种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传播问题,是打开了超越自然与社会二分法的事件传播的新空间。”刘海龙甚至认为,库哈尔斯基是从传染病学出发,重新“发明”了一次传播学。
今年疫情期间,刘海龙一直在思考病毒的传播学问题。他认为,“传播”“交通”“扩散”“模仿”都有相似的源头,即观念、物质、能量在时空向度的共享和渗透”。
“只是,传统的传播学强调观念、信息,而忽视物质,将物质和信息做了二分。但在近二十年来,‘相向而行’才是大势。”刘海龙说,承认信息与物质不具有截然分别,那么信息之“传播”与病毒之“传播”就可以被视作同一范畴。自然也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病毒的传播学。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争议始终存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否能有效地支撑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刘海龙看来,数据、模型背后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世界,一切都是可被计算、被衡量的,“这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认为人是可以控制一切的”。
这个愿望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好似永远不会熄灭。
21世纪是大数据时代,但在一个靠数据、模型可以精确预测或者解释大规模人群行为的世界,是需要一些条件的。
“首先数据要足够多、足够好。”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晔告诉《中国科学报》,“什么样的数据算是好的数据?在于你研究问题的样本规模大小、数据收集的方式、采集的数据随机性有没有保证。再比如,数据必须是多维度的,维度越细,预测越准。可实际上,很多数据都会有影响分析的瑕疵和限制。”
“其次,模型的问题在于,现在更新换代不够快,复杂的现实世界会不断冲击现有模型的漏洞,使之预测和判断出现偏差。”吴晔提到,“还有一个难题在于,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科学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以及它的不可重复性。”
可即便如此,数据、模型仍然可以为解释社会行为、解释世界提供多一些参考。吴晔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借助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或法则,并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以及基本原理,它提供了一种传播学研究新的路径。
“最好的数学模型未必是致力于对未来做出准确预测的模型。重要的是它能否揭示我们的理解与现实状况的差距。”库哈尔斯基在书中写道。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邮箱:shouquan@stimes.cn。